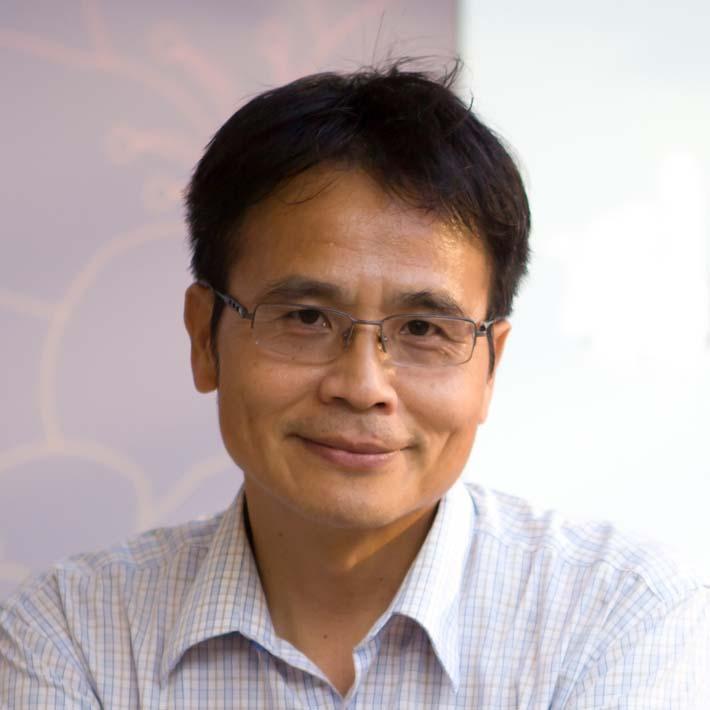虎噬筆記
序
2022虎年,新冠19正狂,我則引發成人史迪爾氏症(Adult-onset Still's disease, AOSD),至今(2026)未癒。方病時,抵抗之餘,無力他務,僅得短語自療。余生壬寅,正逢一甲子,本命遭劫,故名之曰虎噬筆記,於茲姑錄之。
之一
左膝之不適,由來已久。可能廿五歲打籃球時,不慎拉斷部份韌帶,即終身為伴。五十歲開始跑步,起初也頗擔憂,幸好實質影響不大,故不以為意。後跑量大增,成績精進,亦難免各式小故,如左足底筋膜炎,或左膝右膝交替不適等。唯適時調整跑量,妨礙無多。前年(2020)庚子大疫,至辛丑(2021)五月,台灣終未幸免。全島封城自肅兩月餘,我運動不輟,跳繩時,不慎又傷及左膝。該年馬拉松仍有破四水準,但左膝之痛,已難忽視。壬寅八月廿一日。
之二
辛丑壬寅之際,春寒,跑步未輟,唯左膝痠痛加遽。新春返鄉(湖口)前,病情突有蹊蹺。左膝之痠竟然移轉到左肘,此時乃知左膝之痛非關跑步。返湖口數日間,痠痛在諸關節遊走。右腕痠痛時,竟無法挾菜入口;而踝關節痠痛則導致步履蹣跚;甚至某日獨獨右手食指浮腫,其餘關節無事。節後返新竹隨赴□□診所就醫,醫生開消炎藥,並囑開除濕機。不過三天,症狀全消。壬寅八月廿一日。
之三
壬寅五月廿三開練湖口馬,19週的課表,目標是達成「花甲四時」的願望。左膝之痠痛如前,並不礙訓練。六月九與十日小舅子邀登玉山,欣然前往。唯準備不週,又欠經驗,且值賽季訓練期間,頗為辛苦。主峰、西峰及前峰皆攻頂成功,但攻主峰時,全身乏力,勉強登頂;而前峰之亂石更讓左膝吃足苦頭。六月廿五及廿六日,文學地景課程赴屏東校外教學,在淺山步道滑了一跤,又傷左膝。壬寅八月廿一日。
之四
起初以345目標備戰湖口馬,亦即3小時45分完賽。開練之後,總在低標之際徘徊;七月決定降低目標為400完賽。七月十日27公里長跑,當天有行程,於是清晨四點半便起床開跑。後半程強迫身體加速,以達成目標,最後以610完成,亦即每6分10秒跑完1公里。事後看來,此即宣告大事不妙了。隔週正逢課表減量,順勢大休,週跑量僅達40公里。又隔週,勉強按表操課,至週末27公里長跑時,僅19公里就狼狽地放棄了。整個七月行程滿檔,最後一週竟然多達12個行程。至26日耐速力訓練,1600公尺六趟的長間歇跑,跑了三趟就放棄了。就是這一日,正式宣告虎年出生的我,遭虎噬矣。壬寅八月廿一日。
之五
七月最後一週開始自行服用消炎片,起初先服普拿疼。廿七日赴客委會開會,下午結束時,已感覺發燒。夜裡發作,全身畏冷發抖;服普拿疼後,發熱並流汗,症狀才退去。之後幾天,症狀越來越明顯,決定推掉工作。八月四日再赴□□診所,吃了幾天葯,效用不大。八月八日掛到馬偕門診,新冠19快篩陰性,抽血後,要再待廿二日才能複診。病況難以等待,八月十日得友人協助,掛到台大新竹醫院免疫風濕過敏科□□醫師。壬寅八月廿一日。
之六
八月十日求診台大□□醫師,疫情期間,距離頗遠,問診而已。開了消炎藥,抽血五支,並照X光。兩天後,週五複診,開「滅殺除」及其他藥物,名字恐怖。醫師看過驗血報告,再依我敘述病情及目視四肢玫瑰斑疹,認為是「成人史迪爾氏症」。還告訴我可以上網查詢病名及相關訊息。壬寅八月廿一日。
之七
八月十五日回診,將8/12-15病況發展情況寫成字條,讓醫師參考:
8/12 上午看診;10:30突然開始發燒,39.4度,全身冷得發抖;隨後慢慢感覺發熱;最後開始流汗,症狀緩解,全程約90分鐘。期間簡單午餐,並服用滅殺除等葯。(按:實際上此時已開始服用類固醇,我當時不知。)
8/13
自前一天下午至今日傍晚,都很舒服;但18:00再次發燒,感覺冷,但未發抖;也相同地微熱,大量喝水,流汗後緩解,全程也是90分鐘。此時在外家庭聚餐,症狀屬輕微,但病發後,行走困難。
8/14 未發作,行動方便一些。
8/15 目前未發作,但今早醒來,大小腿皆無力,難以步行。早餐後服藥,情況稍好,自行步行到院抽血。
以上。壬寅八月廿一日。(按:我把上述字條遞給醫師後,醫師仍然要我口述病況,並未閱讀。)
之八
八月十二日之發作是病來最嚴重者;十三日與女兒在青草湖邊的餐廳晚餐時,微微發作;之後,病情似乎輕微一些;保險起見,仍持續辭掉行程以減壓。本以為病情就此舒緩,不料十五日回診之後又發病,幸好未像十二日那般全身發抖。更沒想到十七日起,喉嚨發炎,竟致無法言語;之後每天早晚各發作一次,雖不似八月十二日嚴重,但頻率增加,而且四肢無力的病況反而加重。壬寅八月廿一日。
之九
八月廿日週六,上午發作,高燒至39度,驚覺病情似乎見不到底。下午稍緩,寫信或去訊四個單位,辭掉四個工作行程,感覺壓力再小一些。本週鎮日無精打采,人生少見如此只是閒坐、看電視、聽YT影音打發時間而已。廿一日上午微熱,37.5度,差不多等於沒發作,只是昏沉沉罷了。趁著偶爾精神略好,寫了九條筆記。壬寅八月廿一日。
之十
病情摘要8/16-8/22(回診用)
1.本週一天發燒兩次,分別為早上六點左右及晚上七點左右;
2.最高燒是8/20早上39度,其次8/19早上38.4度,其餘37.5上下;
3.發作時四肢無力,最高燒時,腰背肌肉也痠痛,步行困難;但是不再如上週全身發抖;
4.一天僅有兩小時左右有工作能力,其他都無精打采;
5.8/17開始無法言語,喉嚨聲帶發不出聲音;目前(8/22)則沙啞且費力。
壬寅八月廿二日。
之十一
許久未量體重,今晨餐中秤之,竟然只有63.4公斤,不可思議。先前以為「大腿變細」只是目視錯覺,今始知月來四肢無力與發燒是肌肉流失的真實。看來,我這真真實實的人生下半場,關於身體,已不得不打掉重練了。亦哀亦喜。壬寅八月廿四日。
之十二
本週(廿二以來)病況又優於上週,本以為更接近康復,但昨(廿六)日又發燒至37.7度,近十一點才就寢,並加服一顆普拿疼。今晨醒來,狀況仍只普通而已,但這是週末,應該要回湖口了,何況剛好有公務,於是除處方藥外,決定再加服一顆普拿疼,才出門。回湖口家一趟,一切正常,父母並未發現我身體有異,算瞞過去了。壬寅八月廿七日。
之十三
病發之時,周身無力,四肢尤甚。求涼臥地,竟難以起身;自沙發起立,亦有困難;想從床上起身,尚須百般設法。自眠床步行往浴廁,僅能左右搖晃,狀如僵屍前行。赴臺大新竹醫院就診隔週後,病情有所進展,肢體無復僵直難行之苦。本週廿二日晨起,開始嘗試輕微運動。由家中散步至舊社橋下,全程約一公里,雖稍有勉強,但已可應付。目前步行七次,少則二十分鐘,多則一小時,循序漸進之。壬寅八月廿七日。
之十四
發病以來,幾乎推遲或取消了所有行程,新進工作邀請也一律婉辭。於是這幾週是畢生以來,唯一「無所是事」的經驗,十分不慣。發病之時,固然全無工作能力;緩和之時,也往往昏沈渾噩,失魂落魄。稍見精神渙發,一日約兩小時,正好處理一些緊急工作。今日頗有康復之感,也只是完成兩三件無關痛癢之事,亦莞爾。壬寅八月廿七日。
之十五
五週發病以來,似乎直接宣告人生進入下半場了。病前雖亦不諱言自己已年近花甲,但只把六十視為第二中年的高峰,身體工作皆無掛礙。然而,此番病來,全身乏力,起止步行,皆有困難。日後萬一未能恢復,則龍鐘老態,已難避免,豈不唏噓?壬寅八月廿八日。
之十六
週日.陰,八點左右感覺身體狀態明顯優於清晨,於是設定Garmin Sports的30分鐘快走,嘗試運動看看。穿過舊社橋下,於籃球場折返。去程不諳快走姿勢,回程則熟悉,10分速完成三公里,剛好是計畫水準之下標。確實有運動的感覺,令人喜悅。壬寅八月廿八日。
之十七
本週(廿二至廿八)病況又比前週稍好,廿二與三晚上小發作,分別為38與37.7度,略感不適,加服普拿疼。之後幾日則持續低溫發燒約37度而已,並無大礙,且已可連續工作三小時。廿九日復診,醫生決定藥物減量,也暫緩施打生物製劑之議,待續觀察。自評復原程度已超過六成,開學工作,應無困難。壬寅八月廿九日。
之十八
虎趁虛而噬者三,其一,工作壓力大;其二,睡眠不足;其三,運動過度。關於跑步,十年以來,按部就班,累積充分,尚稱謹慎將事,本來不應有故。此時痛遭虎噬,應係2019六月以來,執行漢森訓練法(Hanson Method)不當所致。漢森之強度與跑量可觀,輕鬆跑皆以10公里為門檻。我求好心切,以345甚至330為目標訓練。其輕鬆跑之配速雖可勝任,但其實並不輕鬆。於是身體疲勞尚未完全恢復下,接著又進行高強度訓練,疲勞便不斷累積。漢森的策略就是在這種不斷面對極限,突破極限,而擴大極限中,讓跑者逐漸強大。斯人也,肉身已近花甲,痴念卻猶壯盛;更何況整體工作與作息由不得人,終究在極限前倒下。夯枷!乜係堪該!自家好!壬寅九月初三。
之十九
本週(八月廿九)前段良好,但週三夜發作,週四39度,週五38度,週六38.4度,且明顯地晨昏各發作一次,四肢無力的感覺再度來襲,令人擔心。低溫發燒之時,尚且正常行動,也可處理簡單而具體之文書工作;但38度以上時,又成病人了。昨夜去信社大,請延後北埔兩場演講;原本有一台日學者水資源計畫有兩日中部田調,可能也要婉辭了。本以為本週藥物減量,病情也將改善,但原來不切實際,只是太樂觀的想像罷了,只得再跟醫生討論後續治療。壬寅九月初三。
之二十
關於工作,首先,常規之教學與研生指導其實已經是一個全職教師的工作量了。而實際上,我也努力成為一個認真的老師,尤其是研究生,特別是碩士在職專班學生的指導方面,我付出了可觀的時間。其次,在研究方面,我的客家與人類學議題研究計畫長期穩定地進行,所佔時間不若教學,但固定的撰稿、修改及出版,所花的時間仍然不少。再來,更多的可能是專業服務計畫,長期有2-4名專任助理在計畫團隊中,工作量不言可喻。最後是演講、審查乃至顧問等工作,我往往不太能推辭。綜合以上四項,被工作壓垮只是早晚而已,而它終究在壬寅盛夏發生。壬寅九月初三。
之二十一
十年前跑步以來,視之為修行,雨暑不輟,乃從而體驗自我與形體之密切關係。只是雖視為修行,但難脫對肉身之眷念。丁酉(2017)以來,瑜珈及跑步,深思尤多,似有所悟。然而此番遽遭虎噬,雙腿萎縮,步行且難。病如此,則先前肉身與自我之了悟,已渾不知矣。壬寅九月初四。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