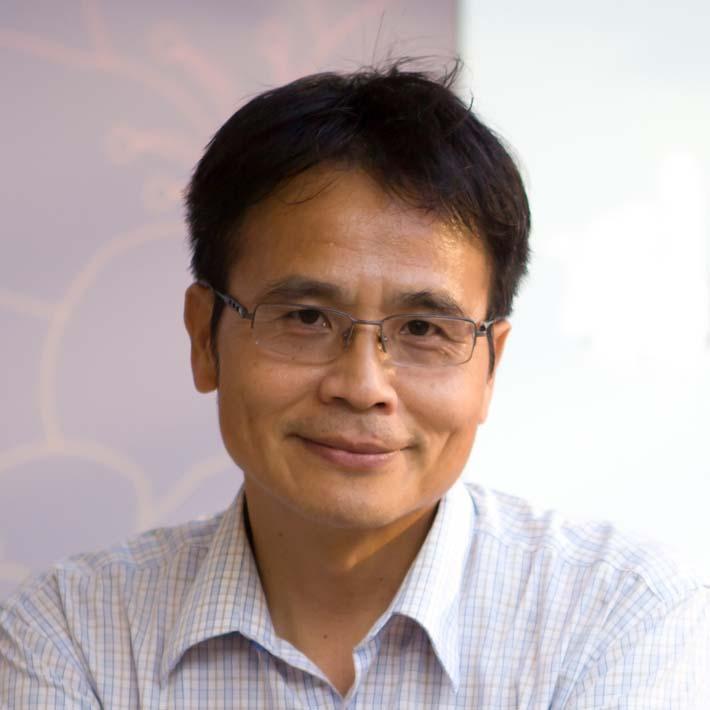歷史、記憶與族群:
羅烈師
2004/3/23
今天的演講正逢總統大選落幕,然而凱達格蘭大道至今沸沸揚揚,顯然選情不會這麼快結束。這場被定位為割喉之戰的大選,始終摻雜著濃濃的國家與族群認同的氣味,儘管我的演講與選舉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某種程度而言,我認為自己試圖在此思考它的起點。我所謂的起點是說,我認為我們對目前現象的理解,基本上必須回溯到台灣族群的歷史。
為什麼定題為1786年呢?因為枋寮義民廟的故事從這一年開始。如各位在導言上所看到的1786年其實發生了很多很多事情。到底這些事情哪一些後來會是成為重要的?哪一些是有意義的?哪一些是後來變成歷史事件?或者是最後甚至變成一個我們記得的部分?或是它會變成我們台灣所看到的族群論述的事實?這麼多事情當中為什麼有一些會是?有一些不是?它背後的邏輯原因是什麼?我嘗試處理這一連串問題。所以我的題目叫做「1786年冬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今天的演講包含四個部份,首先,我們發現竹塹地區關於記憶中的1786年之後的那一段事情有一些不同版本,這些版本彼此重點不同,某種程度是相互函括的,我舉了樹杞林志、文化局出版的《義民心鄉土情》、網站上常常看到的一些鄉土教材以及一般傳說所提到的義民爺傳奇。其次,看過這些版本後,我第二部份嘗試用一些史料,來看「歷史的真相!」,我故意用驚嘆號,意謂「上面說的那一些不同的版本其實不是歷史的真相!」然後我們進入第三個部分,我改了標點符號,「歷史的真相嗎?」這個部分應該是今天演講比較核心的地方,但也必須坦白的和各位說,也就是正在處理的地方、正在思考的地方,我不認為會有一個完整的答案,剛好利用這個機會跟大家來做討論,這也是所謂「大聲的思考」,把自己的想法講出來,大聲地和大家一起思考。
一、竹塹記憶中的義民歷史
1786年臺灣中部發生了「林爽文事件」,清朝的論述會說這是造反、叛變,中國大陸則稱之為農民起義,當然也會有人相信林爽文企圖建立台灣主體意識。這個事情發生在1786年,事後就有很多相關的論述,在往後的歷史呈現出來,也創造了不同版本的義民廟史。
我們先談十九世紀末的「樹杞林版」,這個版本的重點在談「陳資雲」。陳資雲有志要平撫這場亂局,然而他卻沒有多少資源,於是找了一些富商鄉紳協助,後來他們果然就做到了。原文如下:
乾隆五十四年,土匪林爽文作亂,雲(陳資雲)遂慨然有平賊之志。但家貧無資,乃與同莊劉朝珍及六張犁莊林先坤同謀舉義,團練鄉民作為義勇。當時劉、林皆巨富,所有行軍需費皆劉、林備出。於是陳、劉、林率帶義勇出與賊戰。無如寡不敵眾,炮火鋒刃之下,義民戰沒數百人,乃退而駐紮六張犁及員山仔各處要害,把守周密,方保內山一帶地方免遭賊害。幸而固守未久,天兵渡臺,一戰破賊,上下義民出而夾擊,賊遂北,克復竹塹城池。上為國家,下衛地方,厥功偉矣!但陳、劉、林諸人,哀恤陣亡之士,殊抱我生眾死之憾;撫哀自問,其何以安慰英靈於九泉之下。計惟遍尋戰沒之骸,拾聚堆積如山,牛車載回,為覓佳城。果然天保祐之、人愛敬之,即有枋寮莊戴元久施出吉地一所,遂擇吉築墳,鑿穴如倉,將該忠骸聚葬於此。此穴極佳,推冠全臺。而又為建廟宇,劉、林又施出田租,歲時祭祀。而平臺統帥福中堂題請褒封,御書「褒忠」兩大字。而陳、劉、林俱欽加五品頂戴榮身。嗟嗟!我粵東義民之名,千載下猶令人齒頰流芳。此義民廟之祀典,較之諸祀典為尤盛也,固宜。[2]
其次是出版於西元1989年的《褒忠義民廟創建兩百週年紀念特刊》及2001年的《義民心鄉土情》,這些講法可以說是義民歷史的標準版本,它很具體的從乾隆51年,也就是1786年開始,交待義民史實,而且把重點放在竹塹圍城這件事情。林爽文事件時,竹塹城被攻下來,然後竹塹城又被光復。誰光復的呢?客家人光復的。他們光復竹塹城後,又隨軍南下作戰,平定了林爽文之亂。這些犧牲性命的戰士受皇帝「褒忠」聖旨的獎勵,鄉人將屍骸運回,而牛車走到某一個地方就不走了,於是居民問卜,得知義民要求在這裡安葬。其後熱心的鄉民在此營造了墳墓,又建了廟。這樣的故事常被一些鄉土教材所繼承,我找了其中一個鄉土教材,它很生動、鮮明的將義民軍的狀況做一個說明:第一軍是哪裡?第二軍是哪裡?第三軍是哪裡?第四軍是哪裡?然後最後大家怎樣通力合作拯救了竹塹城。相關論述之原文如下:
枋寮義民廟的建廟原因,實肇因於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的林爽文事件,林爽文起事於彰化大里杙(今台中縣大里市),反清而未復明,且部眾多不肖之徒,所過燒殺搶掠,其北路軍王作陷竹塹城,淡水同知程竣死節,林軍為搶奪糧倉地區而進攻客家莊之六張犁(竹北市東平里)與員山仔(竹東鎮員山里)一帶,客家先民奮起護衛鄉土而組織一千三百餘人之義民軍與戰,不但擊敗敵軍,還應竹塹城內泉籍民眾之請,裡應外合,收復竹塹城,並會同泉籍、平埔族義民南下協助官兵平亂,其間有兩百餘名義民殉難,後由領導人林先坤、劉朝珍、王延昌等收集忠骸,以牛車載回,原欲歸葬大窩口(今湖口鄉),車行至枋寮現址,牛停步不進,乃以焚香禱告後,擲筊杯求示於義民爺,義民爺意欲卜葬於此,便在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捐建義民塚,於枋寮山之「雄牛困地穴」,翌年在塚前建立義民廟,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冬,本廟竣工完成(據義民廟大事記),乾隆皇帝頒「褒忠」御筆敕旨,故義民廟又名褒忠亭。[3]
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之亂,淡水同知程峻在中港被圍自殺,竹塹巡檢張芝馨,在城內被殺。王作受林爽文封為征北大元帥,坐鎮竹塹城。林爽文為漳州人,竹塹城富紳皆為泉州人(大多為泉州王世傑之後。)受盡勒索,每日獻金獻糧,苦不堪言,乃暗中求助城外庄堡之客家軍。同時清吏壽同春詐降王作,亦與客軍密謀,擇機反攻新竹。新埔部分客家軍,曾入洪門會及天地會,基於林爽文乃天地會首,乃派員與王作談判,但王作姿態甚高,以滅粵為指日可待,且王作軍紀敗壞,殺人掠奪,搶割稻穀,強搶民女,種種不法。客家軍終於五十二年冬,聯軍攻竹塹,轉戰後龍、苗栗,渡大甲溪,戰至彰化,與清將福安康會合。當時客家軍有四路,竹塹泉州閩軍一路,共五大軍。其餘四軍,有鍾瑞生為首之苗栗軍,北上會合同攻竹塹。第二軍由六張犁富紳林先坤率領,近二千人,在金山面一帶,先據堡柵防守,勤練武功,後傾巢而出。第三軍以新埔陳資雲為首,與林先坤配合,陳資雲戰死,可上義民正主神位,其餘林先坤以下,則為施主,可享長生祿位,其為先烈英雄則一也。第四軍由蘇敬彩率領,北攻大嵙崁,以防北部閩人南下助林爽文,故林爽文之亂,至竹塹為止未再北延。[4]
此外,後來有一些傳奇版本,這個版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說:日本人來了,廟被燒了,但是鄉民後來又重建了。這個版本最被津津樂道的是1937年之後皇民化運動,日本人曾經想要把全台灣的寺廟全部都廢除,並且沒收廟產,但是日本官員所乘坐的火車竟然出軌了,它們接收的官員都坐在火車的前面,一般的旅客是坐在後面,結果火車翻到鳳山溪下面,但是只有前面的列車翻下去,後面沒有翻下去,所以義民爺保護大家。原文如下:
日據時代,台灣處於日本皇民化時期,日本政府有廢除義民廟的念頭,於是日本政府從台北派兵南下至竹北,火車行經鳳山溪最深的地方時,日本人坐的車廂竟從鳳山溪橋上掉落到山下,但後面非日本人坐的車廂依然在橋上且都連結在一起。在當地有權勢的人向日本陳情敘述著義民廟是保鄉衛民的忠義之廟,裡面祭拜的義民軍乃是為保鄉衛民而戰,以「忠」字為義民廟之精神,因此日本人才准予此廟保存下來,度過了廢廟的浩劫。宗教信仰平時不易看見其力量,但在國家有危難時,就會顯現出來。[5]
這些版本彼此之間前前後後,可以編織出一個義民廟史的標準版本。不過,這些故事的真實性如何呢?我們不妨用史料回答這個問題。
三、歷史的真相!
這些版本是真的嗎?我們回到史料,挑幾個片段來分析。第一個讓我最意外的事情是「竹塹城被圍,然後客家人解救了城內泉州人」這件事情。依據《新埔鎮誌》的記載,關於竹塹圍城這件事的始末是:林爽文之亂時,淡水同知程峻及竹塹巡檢張芝馨戰死,王作被封為征北大將軍,坐鎮竹塹城長達一年。由於林爽文是漳州人,而竹塹城內多為泉州人,泉州人受盡勒索,於是暗中求助城外的客家軍。新埔部份的客家軍亦入洪門及天地會,於是便入城與王作談判。結果王作姿態甚高,以滅粵為指日可待,於是後來竹塹的客家人就團結起來,最後終於將竹塹城給光復了。
為什麼我說讓我意外呢?我去看淡水同知陳培桂寫成於西元1871年(同治十年)的《淡水廳志》,很驚訝地發現一件事:竹塹城只被佔領了七天,不是一年!剛剛講的那段故事,聽起來好像很慘烈:王作軍紀敗壞,燒殺擄掠,以滅粵為目標;而客家則為光復竹塹城,兵分四路,犧牲慘烈。可是,史料卻說竹塹城只被佔領了七天,而不是一年。
竹塹城陷一年的記憶,也就是從1786年冬天到1787年冬天,這一說法首先見於1976黃奇烈所編篡台灣省新竹縣志,而後被林柏燕的新埔鎮志所繼承。不過,參考彰化縣志、淡水廳志、台案彙編及高宗實錄等史料,1786年冬季城陷前後半年的歷史大致如下: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林爽文起事,三日內即攻下彰化縣城,並且隨即於十二月初七日攻陷淡水廳治竹塹城。林爽文在中部起事之後,北部隨即擾嚷不安,並非林爽文用兵神速,實係大甲溪以北,從貓盂(今苗栗縣苑裡鎮)到新莊(今台北縣新莊鎮)四方依附者甚眾所致。十二月的前半個月可謂烽火遍地,初八日林小文等燒毀新莊巡檢署,新莊、擺接(板橋)、八芝蘭(士林)、滬尾(淡水)、八里坌(八里)等處亦遍插林爽文旗幟,對據守在艋舺(萬華)的官兵略呈南北夾擊之勢,而且這樣的局勢持續了這一年的整個春天。
這期間竹塹城的情形如何?令人意外的是,實際上竹塹城易主的時間僅有一週,即十二月初七至十三日。事變初起,淡水廳同治程峻率兵馳赴中港(苗栗縣竹南鎮)守禦,聽聞彰化縣城失守,於是準備退回竹塹城。此時四方響應林爽文者眾,程峻誤中埋伏而死,於是竹塹城遂於十二月初七日陷落。程峻的重要幕賓壽同春也於城陷後被俘,依淡水廳志壽同春列傳所記,城陷之時,壽同春已高齡七十,林爽文的北路將軍王作誘勸壽同春投降。壽同春佯裝答應,卻私下派人命令把總陳興世揚言內地大兵已至,又有義勇內應,而同春遂趁隙脫逃出城。後有前榆林令孫讓糾合義勇一萬三千,力圖恢圖,於是壽同春與前竹塹巡檢李生椿等人率軍經三日征戰,於十二月十三日奪回竹塹城,王作伏誅。
(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十有三日壬子,幕賓壽同春等,起義克復淡水,擒偽官王作等正法。初,淡水賊王作、林小文等,既陷塹城,劫奪倉庫,僭居廳事,偽號天運。以賊五千屯踞後龍、樹林頭莊把總吳洪不屈死。又掠被害同知程幕友壽同春不殺勸降;壽佯許之。潛遣人揚言內地大兵已到,賊多疑散,遂約原任竹塹巡檢李生椿,書院掌教原任榆陵縣孫讓,糾合義民一萬三千餘人,收復塹城,擒偽官王作、許律、陳覺,磔於市斬鄭加首,然後上書督撫申其事。[9]
乾隆五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閩安協副將徐鼎士等,領兵渡海,抵淡水後,駐紮於艋舺,前有大河環繞,又有義民萬餘人,協同守護。林爽文淡北與塹南的部眾則約萬人,合聚甘林陂(台北縣土城鎮)。局勢至三月開始有所變化,十二日爽文部眾攻打三角湧(台北縣三峽鎮),游擊吳琇率兵救援,於是雙方在甘林陂大戰,同時在三重埔(台北縣三重市)、錫口(台北市松山區)、艋舺(萬華)、和尚洲(蘆洲),也都有戰鬥。至二十四日官兵克復甘林陂,二十五日退據白石湖(內湖)的最後勢力投降,林小文縛殺。至此,林爽文在淡水廳的勢力已遭撲滅。
雖然林爽文事件是個反政府暴動,各地義民也確實受政府官員之招募而起兵撻伐,然而淡水廳半年的騷亂卻也充滿分類械鬥的濃厚意味。前述戰鬥的核心區位於目前板橋附近之大台北郊區,也就是漳人村落之所在。因此即使林小文已喪命,同年五月份白石湖庄附近漳、泉、粵人仍分庄互殺,於是五月八日,新任淡水同知徐夢麟,會副將徐鼎士,都司朱龍章,及幕賓壽同春,同抵白石湖山下,安撫居民。至此,淡水廳才未再發生戰鬥,徐夢麟也於六月八日迅速進兵屯駐大甲,清廷確定地將林爽文之亂控制在南台灣,並且形成反包圍的態勢。
職是之故,這半年的歷史顯示,林爽文事件雖然使得淡水廳治竹塹城陷落,但是為時僅僅一週,而後續的戰鬥也都發生於台北地區,而非新竹地區。竹塹地區義民基本上是受號召而征戰外地,最顯著的例子是「蘇敬彩北征大嵙崁」,敬彩所參加的戰役應即為乾隆五十二年三月三角湧一役。另外如楊梅總爐主陳泰春宗族的第十四世祖先陳殿朝「…因閩族匪魁林爽文叛亂,廣東粵族陳紫雲義烈勇士援助官軍組織義民軍後援,其時殿朝公奮勇參加戰鬥,在台灣省北部大嵙崁觀音亭附近作戰,不幸戰死,殿朝公骸骨在新竹縣新埔鎮枋寮里褒忠義民廟一同合葬,永為蒸嘗。」
第二個故事是關於林、劉二施主在整個義民廟史的地位,枋尞義民廟現在是台灣一個很重要的祭典區,大到包含全部的新竹縣、一部分新竹市、以及南桃園包含楊梅、新屋、觀音等地方,他們的管理機制叫做管理委員會。這個機制裡分十五個大庄,十五個大庄有三十三個管理委員,管理委員裡面基本上就是十五大庄裡的人,但是有兩個例外,這兩個人就是林、劉二施主,他們是當然的委員,和其它十五大庄的委員共同組成管理委員會。所謂林施主及林先坤,劉施主即劉朝珍(1759-1828),為什麼這兩個人這麼重要?我們先看1865年的史料:
同治四年,林劉施主爰集聯庄紳土,選舉管理,坤等將契券交管理人權放,其管理者三年一任為限,限滿仍將契券交出施主點交新管理人領收清楚。此乃四庄輪終而復始,為管理者自當秉公妥理,日後嘗祀浩大,以增粵人之光;再議章程,立簿三本,將褒忠嘗之業大小契券古今承買,須要契白抄錄於簿內…此係通粵之褒忠嘗,有關全粵之大典,各要忠心義氣以經理,不得私自貪圖以肥己…[11]
前述史料首先回憶了林爽文這個事件的故事,很清楚的將廟的財產請外庄來做管理,這個部分是有一點複雜的,在此我只簡單的說,義民廟有很多財產,需要有人來管理,管理的人要把這批財產分成三本,這個財產的本子抄成三本,其中一本要放到姓劉的施主、一本要放到姓林的施主、一本要由管理的人來負責,所以在1865年時,林劉二施主已經是管理機制裡的重要角色。
我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為什麼1865年時,林劉二施主那麼重要?我們再上溯義民廟的相關史料,結果發現到一件很特別的事情:1802年有一份史料,〈同立合議規條簿約字〉,這個史料最末有四個人王廷昌、林先坤、黃宗旺、吳立貴,這四個人就是所謂的四姓首事。這四姓規約在義民廟史上十分重要,我認為可以看成是枋寮義民廟的憲章,由於過程有點複雜,這裡不談,只討論與林劉施主有關的部份。四姓首事中,並無劉朝珍;但有林先坤,也就是目前的主任管理委員林光華先生的祖先。為什麼廟史初期明明是四姓首事,後來卻只剩林姓,而且後來再加上劉姓呢?林姓施主的部份我們等一下談,先討論劉姓施主。簡單地說,姓劉的施主在廟剛開始建起來的那段時後,其實他沒有這麼重要,一直要到西元1817年(嘉慶二十二年)劉朝珍捐了一塊土地後,他的重要性才開始增加。但是他的重要性是怎麼樣增加的呢?我們看看義民廟史上另外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林茂堂等請帖」,文件表明:「緣枋寮義友祠墓,昔年承戴元玖公捐基,因而林先坤公、王廷昌公、劉朝珍公等倡捐鼎建,并捐田租水穀,以為修理祠墓及香燈普度之資。」這段文字雖然略有疏漏,但大致符合目前我們在文獻上所發現的證據。而且依文獻所顯示,劉朝珍的地位並沒有高到可以變成林、劉兩個施主。如果我們把這個文本看成是義民廟創建近一甲子後的歷史記憶,這段文字顯然隱涵了一個歷史的結果。我們參考其他古文書並仔細推敲原文的意思,係指林先坤與王廷昌倡捐鼎建,劉朝珍則捐田租水穀。然而修辭上卻「交錯行文」,使得劉朝珍也似乎成了倡捐鼎建之人。簡言之,劉朝珍捐施田租於建廟後近二十年,三十年後他已被視為義民廟的倡建者,再過二十年他成了義民廟最重要的兩個施主之一。自此以後,「劉朝珍很重要」的這一模糊印象就逐漸擴大到整個義民廟史,劉朝珍便成了義民軍首領、義民廟的創建者及義民廟的捐施者。現今所見史料,首開其端者為前引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的樹杞林志,而這樣的理解也廣泛地被許多相關客家網站所引用。
這就牽涉到集體記憶的問題了,不同時代的文本書寫突顯了某一些人的重要性,也相對抑隱了其他人,而這樣的文本後來就成了歷史記憶,也成了人們所相信的歷史。就像建廟初期的四姓首事,至十九世紀中期的文獻還保留了王廷昌,但是其他首事不見了,而更重要的是,原本劉姓施主沒那麼重要,這時候他卻重要了。這樣的特性更明顯地表現在「林姓施主」身上。
林先坤來台後先後購得大批土地,也取得六張犁與員山仔溪北犁頭山隘邊草地的開墾權,並率族眾開濬六張犁圳,灌溉六張犁、鹿場、小麻園子、土牛溝頂、下斗崙、泉州厝、紅毛田等莊(俱在今日竹北市內)160餘甲的田園。此後,隨著以六張犁為核心的農墾區逐步發展,林氏族親散居於廣義的六家地區,甚至擴及鄰近頭前溪中游的芎林、南岸的新竹、竹東及鳳山溪北岸的新埔等地,至18世紀晚期林氏漸次成為竹塹地區的活躍角色。相較於劉朝珍,林先坤的地位顯然重要太多,甚至似乎無庸置疑,而且這一點在1788年一份關於義民廟地的契約上,更是明顯。該文獻上,林先坤的頭銜是粵東總理,與另一位總理及四位首事共同領銜,跟戴元玖簽訂捐獻土地的契約。 1865年的褒忠廟記對義民廟的財產這樣回憶:
其時林先坤隨建創廟宇爰請戴元玖樂施廟基,王禪師亦經資助,憑依雖有,嘗祀尚無,嘉慶六年間林先坤倡施水田於前座落新社墘東南角水田弍段,至十九年則林次聖施水租二石三,林浩流施水租三石五,林仁安施水租石二,錢子白施水租三石錢茂安、聯共施水租二石,錢甫崙三石,亦共施水租以成美事。至嘉慶二十二年,劉朝珍繼施水田於後座落二十張犁南勢水田壹甲六分六厘弍絲,施出一半之額。由是集腋成裘,子母多權,祀典日盛,春秋二祭,血食豐隆,每歲中元開費不少,如此榮寵實賴皇恩疊錫者矣。[16]
文中林先坤、林次聖、林浩流與林仁安都是林家公嘗,這一回憶顯示,林家的樂善好施,又是粵東總理、義民領袖、建廟功臣,所以才會在義民廟裡佔如此大的重要性。
那麼,林家的貢獻到底多大呢?1802年的<四姓規約>透露了絕大部份的訊息:
……戊申冬平基,已酉年創造,至庚戌年冬,廟宇完峻。辛亥年二月初二日,王廷昌、黃宗旺、林先坤、吳立貴等在褒忠亭四人面算,建廟完竣後,仍長有佛銀二百大元,此銀係交林先坤親收生放,每年應貼利銀加壹五。又廟祝王尚武廟內設席,當眾交出佛銀四百大元,立有託孤字四紙,四姓各執一紙,其銀眾議亦交林先坤收存生放,每元應貼利谷一斗二升,計共利谷四十八石。面議王尚武每年領回養老谷十石,扣寔王尚武利谷每年仍長有谷三十八石,其銀母利,經四姓交帶林先坤生放,三年會算一次。其銀後日生放廣大,林先坤將銀交出立業,作為四姓首事承買褒忠亭香祀。[17]
辛亥年即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義民廟建成後,林先坤生受託放兩筆款項,一為建廟所餘二百大元,每年亦須付出利率15%,亦即三十大元;一為王禪師所捐獻的四百大元,每年必須貼付三十八石利谷。依這一規約,至1802年,林先坤如依當年約定且以單利計算,必須支付六百大元母金,利息三百六十大元及利谷四百五十六石。然而現存的史料僅能顯示,先坤於嘉慶六年(1801)拾月以三百大元,向竹塹社白番魯于改購得新社墘東南角田地兩段,並言明轉施義民廟。兩相對照,有可能林先坤實質上並未支付四姓首事所代表的義民廟為數可觀的母金及利息。此外,除了這兩筆款項外,林先坤還要處理四姓首事各捐施一百一十大元,作為購買祭祀褒忠聖旨與淡水同知程峻香燈業的資金。因此簽定這份合約的主要原因顯然是要解決林先坤代管款項的問題,而解決之道則係要求林先坤的三男林國寶(1770-1841)繼承父親的管理之職。換句話說,1865年文獻所述「嘉慶六年間林先坤倡施水田於前」的說法恐有疑義,以1802年的文獻看來,林先坤實係代表四姓首事處理這三筆款項,而後來林先坤所購土地也應該視為眾人捐施給義民廟的產業,而非完全來自林先坤。
除了城陷與林劉施主之外,義民廟的一些傳說故事,也值得討論。故事是這樣說的:客家軍為光復了竹塹城及平定林爽文亂而光榮的犧牲了,載運屍骸的牛車走到枋寮停住了,問卜的結果是義民要求埋葬在這裡,而這塊地後來被發現是所謂「雄牛睏地」穴。可是原始的史料竟然說:戰爭後死了很多人,而且遍布各地。令人非常震撼的是這些骨骸竟然在野外放了兩年,沒有人理會,鄉人十分害怕,晚上常常聽到鬼哭,所以後來才有人王廷昌趕快來處理這事情。」1788的文獻這麼說:
……茲因塹屬地方陣亡義友骨骸暴露兩載,乏地安葬,惟有戴禮成、拔成、才成兄弟丈義,為人喜施情殷,先年憑價承買彭榮宗兄弟枋寮庄舊社空地一所,併帶竹圍菜園,地基至門前車路為界,後直至山頂為界,左至吳阿安屋水壢為界,前至車路,屋後直至山頂為界,右至魏阿應浩屋後水壢直透山頂為界,西至彭紹昌屋後石角質透南車路為界。四址分明,即日邀請粵眾到踏看,堪作安塜立祠。卜云:其吉絡焉……
原來這些骨骸竟然「暴露兩載,乏地安葬」,而戴禮成兄弟捐地時,眾人會勘之後,認為是吉穴,所以在此安葬義民。而所謂戰後收拾忠骸、牽牛停蹄等說法,恐怕也只是傳說。其他如火車出軌的傳說,亦曾有研究者翻查當時台灣各報,目前為止都尚未查得直接的證據。簡言之,竹塹圍城、林劉施主、義民的靈驗事蹟等,用史料來看,顯然尚待商榷。
四、歷史的真相?
我們上述援引史料關於不同版本歷史的討論,並非企圖尋找一個所謂歷史的真相,實際上,我認為歷史的意義不在於真相,而在於它如何被建構?用什麼元素建構?在何種脈絡下建構?它又是憑藉什麼法則?或者,用一句話把它串起來:歷史是「什麼人、在什麼社會脈絡、用了什麼元素、依據什麼文化法則而建立起來的?因此我所說的不是一七八六年以後,一路發展下來的那個真實歷史,而是我們印象中的歷史,真實地在我們生活推動人們的那個歷史。
什麼人:彼此分類的人群;什麼社會脈絡:在一個王朝的統治之下;用了什麼元素:很重要是一個死亡、還有一些儀式性的安排、組織;;什麼文化法則?說明如下。
(一)文化法則
首先談文化法則,我引用武雅士(Arthur Wolf)的1974年出版的《神、鬼、祖先》一書,但略加修改為下表:
|
官
|
神
|
廟宇
|
|
親族
|
祖先
|
公廳/祖塔
|
|
民
|
鬼
|
義塜
|
圖一中路是中國人對超自然階序的看法,相配的有一些社會的組織與信仰的組織。右路是儀式空間,針對鬼有義塚,針對祖先有公廳,就是所謂宗廟、家祠,然後針對神有廟宇;左路則是社會階序的分類,神相對於官,祖先是我們的親族,而鬼就好像是民,這民的意思是比較接近陌生人,讓你害怕的,畏懼的。那麼我們要把義民放進那一個超自然範疇呢?義民是一個孤魂野鬼呢?還是一個祖先呢?一個神呢?如果當時,沒有一個叫王廷昌的人、沒有設塚建廟這些過程,這些殉難者就真的會變成無人聞問的孤魂野鬼。但是歷史的發展沒有這個樣子,他們被祭拜然後埋葬起來,然後甚至被認為是神。可是,我的意思是說,他不能放在普通「鬼」的這樣一個領域裡,一旦放在鬼的領域裡,沒有神格,很難被尊敬,所以要想辦法在這樣一個文化法則下,把它從「鬼域」推往「神界」。
竹塹居民在這一法則下,運用了兩種力量推升義民神格,一個是君王的力量,另一則為人民本身崇信的力量。我們先談君王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則詳見祭祀下文組織部份。林爽文事件後,漳州、泉州、廣東、原住民等四大族群,分別得到「思義」「旌義」「褒忠」與「效順」等四塊匾額,各族群也因此都成了報效朝廷的義民,其地位也因君王的權威而提升。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君王的匾額原本是應被懸掛在通衢大道,作為坊里牌,可是臺灣漢人卻直接將它做為祭拜的對象。這個現象用當時的詞彙叫「聖典」,聖是聖旨,典是儀典。目前我們至少可以看到兩個聖典的例子,首先是枋寮義民廟,1801年的四姓規約非常重要的一個目的就是聖典。四姓首事各出一百一十大元買一塊土地,原因是為了祭拜聖旨和殉城的淡水同知程峻。第二個例子是高雄大樹鄉,「(林爽文)事平,清廷御書「旌義」兩大字以表其功。六莊莊民挨次流交,每逢十月初二輒設香案,高懸檀上而朝拜之。是日,梨園數十臺、酒餚數百席,以為義民普云。」藉由聖典,居民把對聖旨的朝拜轉移到殉難義民,無形中營造了義民為帝王所封,從而晉升為神為氛圍。
也正因此,義民的超自然位階相當不確定。首先,他們不是鬼,他們的骨骸被安葬在吉穴墓地中,他們的名字以一共同的名稱「義民」書寫在牌位上,他們歲享蒸禋,不是無主亡魂;其次,他們不是祖先,既無姓名,亦無後代,自難載諸於族譜;最後,他們不是神,因為帝王並未封贈義民為神,更何況而今封神的帝王本身已被逐出漢人的歷史。
然而,他們卻既是神、也是祖先,而且和孤魂野鬼的關係又十分密切。儘管那個封神的年代已經遠颺,但是斯土斯民卻依舊地當他是神一般祭祀,也寫在調單之中;他們雖然大都無後,但是卻也有極少數例子身後留有顯赫宗族;至於鬼魂方面,屬於義民年度最大的祭典「慶讚中元」,十五庄輪值辦理,所祭祀的對象正是所有水陸亡魂。
(二)社會人群之「分類」
「分類」雖然是現在十分習用的名詞,但是它卻不是新名詞,實際上,清朝的文獻便用這個名詞描述當時的人群分類。枋寮義民廟因林爽文之亂而建立,對竹塹人而言,除了忠君之外,義民同時被塑造成分類械鬥的殉難者的形象,「他們為了我們而犧牲,是我們的守護者!」因為有族群的分類,使得有某一部份的人把它視為保護者,甚至成為保護神,如果不是有這樣一個分類狀況,它的情況大概會有改變。相同的邏輯下,那些率領義民軍、安葬殉難者、建廟、主持祭祀的人,也因此連帶地成為族群的英雄。
換言之,如果不是臺灣漢人社會原本就存在不同祖籍的人群分類,又如果不是帝國自始至終都以族群政治穩住其帝國政權,那麼義民信仰將會是臺灣漢人的普遍信仰形式,並不會特別帶有客家色彩。實際上,如前文所述,義民信仰中本來就同時存在著「旌義亭義民廟」與「褒忠亭義民廟」,然而正因為族群之間的緊張關係,促使義民信仰不斷為客家所推崇,甚至使義民信仰成為一種客家的信仰。這種趨勢的高峰一波高過一波,而近年臺北市客家的義民祭典裡,關於興建義民廟的急切呼聲,正可謂再掀義民信仰之壯闊波瀾。
(三)祭祀組織
前文提及,竹塹居民透過君王封贈權力提升了義民的神格,也就是說,君權提供了義民信仰一個合法性基楚。既然有塚有廟也有牌位,自然需要有祭典儀式崇祀義民,而祭典儀式的最佳保障就是有一份豐富的廟產,憑藉廟產收入來支付祭典的支出。此後兩百年,義民廟正是透過「廟產與祀典雙元管理體制」,在廟產與祀典兩方面,擴大了這個信仰。以這樣的角度觀察,我認為枋寮義民廟經營管理制度史上最重要的一份文件是西元1802年(嘉慶七年)的四姓首事仝立合議規約書,往後義民廟二百年的發展,基本上都不出個規約的設計。四姓規約想要約定的事情很多,站在體制演變的角度看,本約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兩個發展主軸:外庄經理與中元外庄領調。所謂外庄經理意指將義民廟的財務交給外庄適當人選經管;而中元外庄領調則意指每年慶讚中元的祭典亦交由外庄人士前來認領祭儀工作及其所需資金。經過一百餘年的演變,廟產經營之組織從首事、不特定經理、四大庄經理而逐漸演變成為現今的管理委員會與財團法人,義民廟廟產也同時大幅增加。至於祀典則因外庄領調的制度,使得參與枋寮義民廟中元祭典的村庄越來越多,終於成為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規模(參考表一)。
表一 枋寮義民廟雙元管理體制演變表
年代
|
歷史分期
|
廟產
|
祀典
|
資料來源
|
1791-1816
|
首事
|
林先坤(林國寶)
|
四姓爐主、首事
外庄中元爐主、義民嘗會
|
1802仝立合議規條簿約
|
1817-1834
|
首事
|
范長貴、林國寶、姜秀鑾
|
林劉施主、外庄中元爐主
|
|
1835-1846
|
不特定經理
|
不特定經理
|
十三庄爐主
|
1835敕封粵東義民祀典簿序
|
1847-1913
|
輪庄經理
|
四大庄經理
|
十三(四)庄爐主
|
1847林茂堂請帖;1865褒忠廟記
|
1914-2004
|
管理委員會
董事會
|
協議會、管理委員會
|
十四(五)庄爐主
|
義民廟協議會規約;褒忠亭管理委員會章程
|
如前所述,擴大參與是雙元體制的重要成果,那麼這種擴大的效果是如何完成的呢?我認為其中的關鍵是枋寮義民廟創造了一個階序體系,正是這個階序體系將廣大的人群納入它的信仰體系中。這其中的問題相當複雜,可以另外再寫一篇文章,這裡簡單勾勒出綱要。枋寮義民廟的階序體系包含三個層級:管理人、爐主與緣首(參考表二)。這個體系的構成與財產及金錢的捐施有直接關係,以管理人為例,前述提及之林劉施主的當然管理人資格就是其祖先曾經捐施廟產。而且正如施主之名,本來就指的是捐施土地之主人,因此我們可以說這一階序體系與財產息息相關。至於爐主與緣首位階的決定也與金錢之捐獻直接相關,要擔任爐主一定要比別人捐獻更多錢財。而且為了確定其位階,枋寮義民廟的爐主是固定的,而非基於神意。此外,在這階序體系的最下面,尚有更廣泛的人群,義民廟的慶讚中元祭典便讓所有家戶自備飯菜,進行所謂「奉飯」儀式,於是所有人群都被收納到這個階序體系中。
表二 經理/爐主雙元經營體制
|
十九世紀
|
二十世紀
|
經理廟務
|
經理
|
管理人主席
|
管理人
|
委員
|
輪值祭典
|
爐主
|
總正爐主、總副爐主、爐主、總會主、總醮主、總壇主、總普主、總總理、總理、總經理、經理
|
緣首
|
玉皇首、觀音首、三官首、灶君首、五谷首、城隍首、天師首、北帝首、義民首、福德首、集福首、平安首、水燈首、斗燈首、聖母首、巧聖首、招財首、大士首、楊公先師首等
|
五、結論:
看過了這兩百年的枋寮義民廟史,我們回到題目上的西元1786年,到底以上這些討論與1786年的冬季有何關係?我的回答是:1786年發生了什麼事不是被1786當年那個時間點的事件所決定,而是被後來更多事件反反覆覆地重新加以詮釋。
歷史的記憶就是這樣丟丟撿撿的,人們總是接受自己想要接受的,因此歷史的詮釋權就一直變動著,而且歷史的建構是永不止歇的,後面一個事件會重新詮釋上一個事件。最直接的例子是林爽文事件之後的戴潮春事件,其實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義民廟廟產管理組織曾面臨相當嚴重的危機,原來外庄經理模式幾乎崩解了,新埔街連任三屆經理,而未由大湖口庄接任。結果就在那年臺灣中部發生了戴潮春事件,竹塹客家軍再度出征,牛車又載回來一堆殉難屍骨,不可思議地用一個活生生的事件證明從前的歷史事件是那麼真實。事件之後,大湖口庄輪值義民廟廟產經理,義民廟的歷史,特別是財產管理的歷史發生了重大的變革。戴潮春事件使原本很可能會逐漸淡薄的歷史事件(林爽文事件),因為這個事件而重新詮釋,變成真正的歷史事件了。我想或許今晚之後,我這場演講也會成為建構1786冬季以來義民廟歷史的一部份。
那麼,1786年冬季竹塹城陷之後,它是立刻被光復、還是被佔領了一年?我想這是歷史學者的問題,對於那些擎香膜拜的善男信女而言,歷史記憶似乎不是這樣儲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