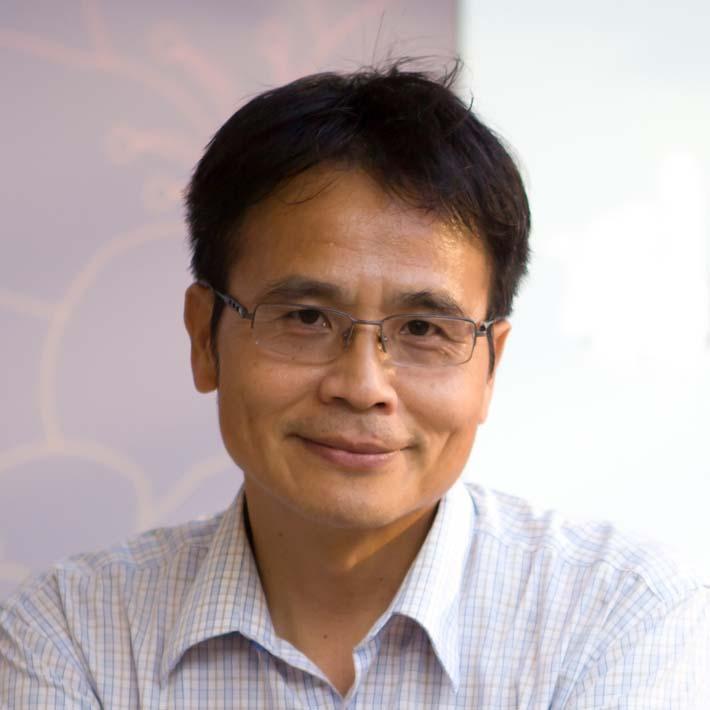•2014年5月12日 星期一,晚上8:38
許福
壬辰正月十五日白天隆重盛大的阿娘出遊後,晚上七點巴剎還有扮神花車遊行。花車上的年輕女子扮成慈悲娘娘模樣,寶相莊嚴,引人頷首注目。隨行尚有地方領袖、民俗遊藝團體、跑車等,並且還有助興的晚會表演及煙火活動,擠得巴剎水洩不通,真是好個熱鬧的年節。
然而,就在這熙來攘往的人潮裡,更重要的儀式就要在巴剎街道邊展開,那就是「許福」。正月十五的許福與十二月初一的還福,是兩個相配的儀式,儀式的主神不只是慈悲娘娘,更有玉皇大帝。許福還福的地點不在廟內,而是巴剎下馬臺與廟坪的篙燈下。
晚上八點半,黃法師率總理與福首先在巴剎下馬臺上香,開始進行許福儀式。下馬臺內設有三座香爐,由高後低,依序為玉皇大帝、慈悲娘娘與五顯大帝,許福的祝文即暫時供奉在玉皇大帝的香爐內。
 |
| 兩封許福祝文 |
第一階段的許福為「合境良福」,許福的對象是昊天金闕玉皇大帝,但請慈悲娘娘轉奏。眾位上香之後,法師開始請神,聖箁證明後,宣讀請慈悲娘娘轉奏玉皇大帝的祝文後,焚化於香爐內,之後辭神,完成第一階段的許福,為時約十分鐘。
接下來的「太平良福」則移往水月宮廟前的篙燈下舉行,包含請神、起篙燈及上表,儀式約一小時。儀式進行前,先移除篙燈下的香燭及雜草後,總理福首上香,法師請神憑箁證明後,開始起燈篙竹。每年正月十五起篙燈,至十二月初一下篙燈,並移去燈篙竹。正月十五日前,要先準備新斬的長竹篙,篙身上設滑輪,以備昇上油燈。由於篙身超過十米以上,二十餘人抬竹,並先固定底部,再借助拉繩,費時近20分鐘,才立好燈篙竹。由於難度不小,動員人力又多,這幾乎是許福儀式最引人注目之處。
 |
| 起篙燈 |
燈篙竹樹立之後,法師誦讀上呈玉皇大帝的「太平良福」祝文,可謂初步完成許福儀式。這時許福儀式中,與起篙燈同樣最常被鄉人提及「埋水碗」展開,這是一種針對篙燈的制煞與潔淨儀式,藉由埋設符令,確保神聖的篙燈不被不祥之物污染。法師手持尖棒,先移開香爐,再以獨特而具有神力的步伐、姿態與手勢,對篙燈下施法之後,挖出前一年埋下的水碗;其次拿出兩個新的水碗,其一盛滿淨水,其上交疊兩紙符令,再以另一碗倒叩後,重新埋入地下,此即所謂埋水碗。
 |
| 法師率總理福首謝神 |
此時,重新安置香爐,並在香爐上焚化呈玉帝之祝文,再由爐主點燈並昇燈。此時法師大喊「發」,眾人應之,然後焚燒金紙,答謝眾神。
正月十五日新立篙燈後,每日傍晚五點將油燈放下,添油點燈後,昇上篙頭;隔日清晨五點放下油燈,熄滅火焰後,再昇回油燈。如此日復一日,直到十二月初一。
仰望夜空,儘管一燈如豆,但絕不寂寞。村民告訴我,1996年曾有人建議將竹製篙燈,改為永久鐵材。理事會討論後,不敢議決,轉請娘娘聖裁,結果連續八次「擲沒箁」,最後保留了這了不得的習俗。感謝阿娘慈悲,我知道那高處暗燈代表著八港門坡眾卑微而虔誠的祈禱,風雨無阻,日日如新。
 |
| 新堯灣傍晚風雨將至的微明篙燈 |

.jpg)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