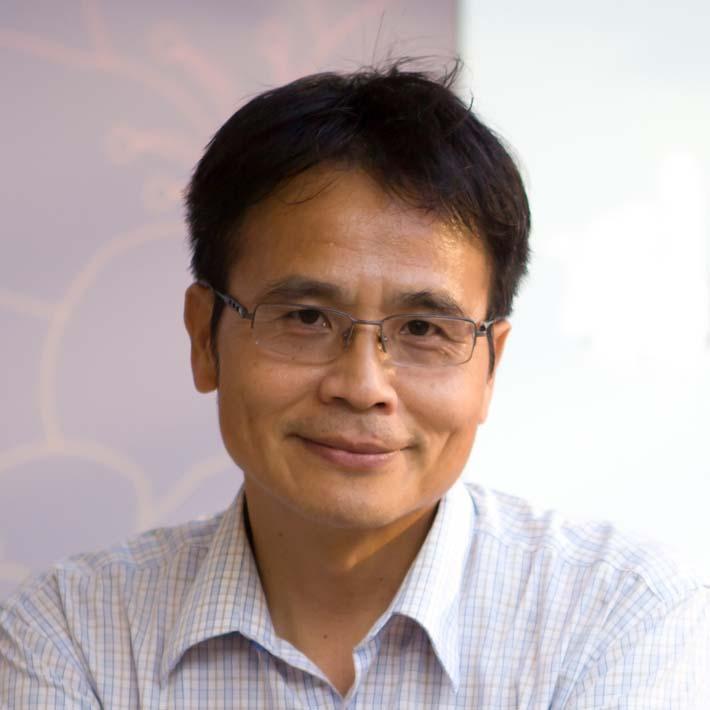英雄與伯公:
砂拉越新堯灣的落童儀式
羅烈師
交大客院
2013.6.26-27
一、前言
起乩係指神明附體(spirit possession)以作為人神溝通之媒介,這一信仰民俗普存於人類社會,馬來西亞砂拉越州石隆門縣新堯灣稱之為落童(log tung)。正值當前砂拉越大伯公節文化論述方興未艾之際,新堯灣亦不由自主地捲入其中。鎮內主祀劉善邦之善德廟在坡眾口中亦稱為伯公,但這伯公與泛砂拉越乃至整個馬來西亞所謂大伯公所指涉的神明並不相同。本文以2012年4月6日晚上7時至8時的一場落童儀式,說明跨地域大伯公節慶滲入地方時,所造成的喜悅與不安。
二、善德廟與劉善邦
善德廟即劉善邦廟,位於新堯灣(Siniawan)附近。新堯灣在東馬來西來砂拉越(Sarawak)州,是首府古晉(Kuching)西邊30分鐘車程的一個小鎮,行政管轄屬馬來西亞聯邦砂拉越州古晉省石隆門縣,主要華人居民為來自廣東揭陽的河婆客家(Hopoh Hakka)。
沙勞越的民族構成包含達雅族(主要為Iban和Bidayu)等原住民、馬來人、華人及印度印尼等。華人佔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多中國南部移民。福州人最多,客家人、福建人、潮州人、廣東人和海南人次之,其他省份少之又少。
就首府與第一行省古晉近七十萬人而言,華人人口佔35.5%,馬來人33.5%,其餘為原住民,又以比達友(Bidayuh)居多。大致而言,華人、馬來人、與原住民各佔三分之一(參見表一)。
表一
馬來西亞砂拉越州古晉省族群人口統計表(2008)
|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
Total
Population
|
Chinese
|
Malay
|
Iban
|
Bidayuh
|
other
|
|
Kuching
|
606,500
|
230,900
|
215,800
|
61,400
|
75,400
|
22,900
|
|
88.10%
|
38.10%
|
35.60%
|
10.10%
|
12.40%
|
3.8%
|
|
Bau
|
49,800
|
10,000
|
4,100
|
800
|
34,200
|
700
|
|
7.20%
|
20.10%
|
8.20%
|
1.60%
|
68.70%
|
1.4%
|
|
Lundu
|
32,200
|
3,500
|
10,800
|
4,300
|
12,700
|
1,000
|
|
4.70%
|
10.90%
|
33.50%
|
13.40%
|
39.40%
|
3.1%
|
|
Total
Kuching Division
|
688,500
|
244,400
|
230,700
|
66,500
|
122,300
|
24,600
|
|
100%
|
35.50%
|
33.50%
|
9.70%
|
17.80%
|
3.5%
|
資料來源:Department of Statics, Malaysia, 2011。
就石隆門縣而言,2008總人口約五萬,其中比達友近七成,華人二成,馬來及其他一成(亦參見表一)。
砂拉越華人史與新、馬及西婆羅洲華人史關係密切,以客家為主的石隆門華人史其實又與西婆羅洲之華人公司之興衰息息相關,十九世紀中期石隆門客籍華人反抗英人統治時,曾一度攻陷首府古晉;位居古晉與石隆門水路交通要衝的新堯灣,正是當時戰場。
二十世紀初期客籍華人在新堯灣建立商業街區(巴剎、Bahasa、Pasar),開啟本區繁華;然而,1965年巴都吉當大橋通車起,由於陸路交通變遷,人口外移而逐漸沒落;當代新堯灣則同時面對文化遺產保存與商業重振的雙重議題。
新堯灣巴剎及其周邊八港門(kampong村落)的主廟是位於新堯灣巴剎的水月宮,水月宮主祀觀音菩薩,陪祀太陽星君、文昌帝君、華陀先師於左神龕;右神龕則有太陰娘娘、註生娘及三奶娘娘。新堯灣巴剎周邊尚有義文宮、水德星君、彌陀亭、義山南山亭與地母宮;各港門的村廟則尚有四座,分別為友蘭路主祀劉善邦的善德廟、港背主祀五顯大帝的福興宮、大山下主祀水頭伯公的福興宮、以及單頭榴槤主祀孫悟空的大聖廟。至於打火石與加蘭依,皆無村廟。另外在拿督公方面,水月宮後方新建排屋及加蘭依下馬臺附近,皆有拿督公,但並未納入村落儀式中;唯一例外的是善德廟旁的拿督公,每次善德廟祭祀時,坡眾皆為同時向拿督公上香。
善德廟的確切興築年代已不可考,是否十九世紀已有小廟全不可知,今廟改建之前確有小廟,而那或許是1930年代所建。目前廟宇規模係1977年起改建,廟內目前仍懸掛當時全體捐款者的徵信木牌,1980新廟落成。
廟內主祀有六神,併寫一神牌上,由左至右依序為玄天上帝、老祖仙師、王三伯伯公、劉善邦公公、劉大伯公公、劉珍珍仙姑,神牌上方則懸掛「三義堂」匾額,此三義應即王三伯、劉善邦與劉大伯三者。
神牌兩側有對聯「義士血淚染山河 義結金蘭定越邦」;尚有己未年(1979)懸掛之「三公建業盟誓百年心身為社稷 義結金蘭功虧一夕血淚染山河」對聯,落款為「弟子黃恩祈敬贈」。
劉善邦即率領石隆門十二公司之礦工,攻陷古晉皇宮,敗走白人拉者布拉克之客家英雄;然而,礦工退守之後,拉者隨後反攻,血洗石隆門。其人野史與傳說言之鑿鑿,然而官方檔案卻查無此人,近來頗引爭議(李海豐 2011)。只是無論其人是否名為劉善邦,其人確實存在,其事亦真有,且從善德廟對聯所示濃烈的國族情感,更可看出此事涉及信仰與族群文化象徵,已非歷史學所可解決之學術議題。
善德廟年度重大祭典有二,一為正月十五隨水月宮慈悲娘娘之八港門出遊儀式,另一則為七月十五日中元之盂蘭勝會。前者儀式進行前一夜,善德廟舉行落童儀式,為所有儀式中使用的祭器開光,以確保其神聖性。同時,開光之後,容許村人問事,解決平素生活瑣事、橫財及庇佑平安等。
2012年春季,友蘭路坡眾修葺廟宇周邊環境,乃提議擴大辦理伯公祭典,開始分頭募集緣金。4月5日值年總理、福首與工作人員,前往水月宮理事會主席家中,在秘書長的指導下,召開4月16至19日(農曆三月二十六至二十九日)祭典活動的行前籌備會。會前同時附帶了有一個北婆羅洲黃金公司(NBG)在友蘭路探勘計畫的說明會,而NBG公司也捐了5,000馬幣,約佔總緣金的四成。
四天的活動排了四日文娛活動,有本地歌手,有外坡請來的名歌手,以及兩日的大家唱卡啦ok,場地布置及器材等,亦耗資約萬元。
然而,散會之際,一位福首驚道:「伯公不知喔!」於是眾人當下決定次日舉行落童儀式,告知劉善邦。
三、儀式過程
本儀式2012年4月6日(農曆三月十六日)晚上7時至8時在善德廟內舉行,參與者包含儀式專家張姓、總理劉姓、黃、李等六位福首、以及陸續前來觀看的老少村民十餘人。儀式過程包含請神、落童、問事與辭神四個部份,其中問事是儀式舉行的目的,而此次於最重要的事情即為農曆三月二十九日的儀典事宜,也順便問了廟地修整之事;另外,也有一位村民為嬰兒祈福而來。以下分項說明此一流程,完整的紀錄可參閱附錄。
(一)請神
接近七點時,幾位福首開始上香,福首李載來「師父」張,總理劉及其他福首也到達並陸續上香。師父年近七十,村夫模樣,以雜工及部份農作為生,兼行落童儀式。
眾人上香畢,師父常服行請神儀式,總理福首及一位婦女帶著兩個小孩一起合十跈拜。先請廟祀諸神,再請四方諸神,最後請開基地主與四方地主;其次表示今日三月十六日,總理與福首等謹備祭品,齊齊跪在案前,為三月二十九伯公生千秋聖誕之事,請問伯公旨意。師父請王三伯、劉大伯或劉善邦公三位之中,一位前來。
三位仙人大德來或未來,師父張以聖筶為評,經第三次擲筶,才獲致聖杯。隨即以秣草水灑淨案座,並且飲一口淨身,準備正式進入落童儀式。
請神之時,眾人發現兩位負責帳務的工作人員未到。他們跟村民朱說自己另有會議,無法前來,偏偏朱又沒來,打了電話又沒接。眾人責怪了頗久,直到下一階段正式落童之後,才停止。
(二)落童
請神之後,師父張換上紅色麻布袍並綁上頭巾,扮成落童。他低頭坐在供桌前,閉目等待伯公附體。這等待之片刻,眾人皆在靜默之中,但兩位福首仍斷斷續續三言兩語地討論著村民朱沒來之事。靜默持續中,落童的鼻息聲越來越大,兩人討論著有件事要記得問。
隨後,師父張搥桌、咳嗽、歎息,顯示神明就要附體。總理關切地問師父張:「恁嗽啊!」(咳得這麼厲害啊!),還有村人替他按摩腰背。此時,師父張拿起錢製小聖筶擲於桌上,第一次笑筶,落童應聲低笑;第二次還是笑筶,總理對落童說:「笑啊,恁歡喜啊!」第三次終於聖筶了,落童拂髥並沙啞低沉地笑了幾聲,此時神明附體(落童)了!總理輕問是哪位到前來,落童低聲用氣音說,劉大伯。落童持續咳嗽,總裡隨即送上特別在街上買回來的茶。
(三)問事
1.祭典日期
眾人其實早已確定陽曆4月16到19四天(農曆三月二十六到二十九)辦理善邦公誕辰儀典與文娛活動,甚至前一日才敲定活動細節,只是這一切並未徵得善邦公同意,故必須落童問事。
劉大伯附身後,總理問道今年三月二十九日伯公生,為善邦公公做戲慶祝,好嗎?劉大伯一擲聖筶即得聖杯,眾人大樂,高喊「伯公愛,伯公愛做戲!」(伯公要啊,伯公同意做戲慶祝。)
眾人歡喜之時,只聽劉大伯以沉穩堅定的語氣鄭重告訴村民:「厓善邦裡廟宮流傳的歷史流傳下來,善邦介生日就係三月初十」(在我們這劉善邦廟流傳下來的歷史,善邦的生日是三月初十)。
村民一驚,交頭接耳之外,又一再向劉大伯確認。劉大伯表示,善邦公的生日是三月初十;不過既然眾人已擇定三月二十九日慶祝,將就在這一天辦理就好了;甚至以後慶祝也都用這一天,不用顛三倒四。
2.儀式與祭品
確定日期後,總理請劉大伯指示儀式的辦理方式及祭品,劉大伯再次拿起聖筶,向其他廟內祀神確認。四天的慶祝活動,以最後一天三月二十九最重要,當天要準備「三牲酒醴、壽糕、壽桃、齋儀果盒、篙燈篙燭」,還特叮嚀廟內要準備清香,以備村民奉拜。
同時,村民更在劉大伯面前商議當天擺設祭品的時間,最後決議當天傍晚五點多全體福首開始進行。對此,劉大伯語氣堅定地說:「汝兜總理伯福首公大家去安排就好了嘛!」
3.寶物
儀式進行至此,主要的目的已達成,接下來則是開放接受問事的時間。第一個問題由福首李提問:後山有没有寶?李提問之時,意味深長且有幾分神秘。一來因為NBG公司才請求村民同意在友蘭路試掘以測量金礦,而金礦本來就是石隆門客家致富的關鍵;同時,劉善邦陣亡前藏寶於此的傳說歷久不衰,近來村人整葺廟地,更勾起這一好奇心。
對此,劉大伯不置可否,任憑眾人再三詢問,僅四兩撥千金地回答:「寶物?有寶物沒?該總理伯收成啊就好了。」(有寶物嗎?如果有寶物,就由值年總理收存保管就好了。)
4.施工(善邦墓)
第二個問題由總理續問能否略略整修廟旁的劉善邦墓?總理係有見於墓土漸漸流失,與眾人商量後,便向劉大伯請教。這所謂劉善邦墓乃係難以證實的傳言,信者會在祭祀之時,也在這抔土前上香。
對此,劉大伯沉默良久,最後緩慢地說:「汝想仰般就仰般」(你想怎樣做就怎樣做)。
總理緊接著問可以施工的日期,劉三伯表示四月份的初三以及其他逢七之日皆可。總理又請劉大伯賜與令符護身,劉大伯隨即施作,由總理交給施作工人。
5.帣印
第三個問題來自村民,請求劉大伯庇佑嬰兒。原本這嬰兒就已佩帶「帣」(囊形平安符),但再請求劉大伯用印在嬰兒身上,予以庇佑。劉大伯便用印在小孩天庭,再做青符,開光之後,擊掌施法,讓家人攜回。
6.施工(廟左前)
第四個問題,總理又續問廟左前方廣場施工事。此係祭典那幾天,會有大量車輛前來,水月宮理事會捐錢僱工,載砂石將該地整平,以確保平安。故此告訴劉大伯,並問有無何事需注意。劉大伯表示「掃淨就好」,意即施工前,先用掃把掃過該地,避久不祥之物即可。
7.舞臺
最後,幾乎就在儀式結束前,總理指向門外,問道慶祝的舞臺就搭在廟門正前方,可以嗎?劉大伯無意見,應道:「放在正位」即可。
(四)退座
至此儀式真的進入尾聲,總理問劉大伯可有任何交待?劉大伯請大家共飲好酒,倒在大杯後,眾人輪流品嘗。劉大伯則趴向供桌,然後喘了一大口氣後,狀甚疲勞地恢復了原來師父的身份。他脫去紅衣紅帽,跟一位晚到的村民說了幾句話,然後要總理燒化紙錢,並向諸神表示所有今夜所有事務皆已完成,請神領受金銀財寶,並即辭神。
四、討論
新堯灣所謂落童,在華人其他社會尚有乩童、童乩、跳童或「上身的」等稱呼,相關研究包含乩童的定義與類型、信仰與傳說、養成、儀式行為、醫療行為、社會網絡、身份地位、概況調查與政府管理等(嵇童 1983:37-38)。這其中,以乩童之居於神人之間,人而非神,神而異人,其中介身份之討論向來是研究的核心。
這一中介身份在「上身的」個案的討論中,視乩童為尚未成神的神,如臺灣與閩南地區如惠安、廈門、金門與澎湖等地,奉親人為神,並充其靈媒,接受街坊鄰舍問事,這些「上身的」是民間的造神運動,而最典型的例子正是媽祖(余光弘 1999: 98;108-109)。簡言之,從人到「上身的」,再到神,乩童不僅是人們的靈媒,甚至可能成為神本身。
相同地,從民間醫療的角度觀察,乩童是一種具有醫者能力的特殊病人,就像其他社會的巫者 (shaman) 一樣,挫折、創傷或痛苦的經驗是他們成為巫者過程中的必經之路,而在自我醫治或接受神療的過程中,他們也逐漸獲得醫療他人的能力,可謂受創的醫者(林富士 2005)。換言之,成乩之前乩童是人,但異於常人。同時,連同前段所述乩童之成神,則成乩與成神可以視為是人們將特定個人予以「神化」的兩個相連過程。
反之,這一面向也可以轉用「神的具形化」,從相反方向討論。乩童一如神像,是一個將神具形化的文化設計。當神以乩童的形式出現時,無疑地更能進入信徒的日常生活中,與信徒的社會網絡連結(林瑋嬪 2002: 25)。也就是說,神以乩童的形式出現,不妨稱之為「人化」,而且當乩童與人們的社會網絡連結時,他是亦神亦人的,那人的形式就是神藉以進入社會的憑介。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人化或神化是兩個相反的討論面向,但對於宗教信仰的研究者而言,信仰行為的行動者終究是人類本身。關於神化的討論重點是人本身在成乩成神過程中的特質;至於人化的討論重點則是人化後的神,其人之具形,對神性產生何種影響。簡言之,討論的核心非神非童,而是人本身。
從這個角度理解,吾人可以從人們與乩童的問事行為中,解讀這其中多重宇宙觀的歸因現象,而這自然也就是人們的信仰宇宙觀(張恭啟 1986)。又或者在極端特殊的集體起乩或著魔(possession)的現象中,吾人可以發現起乩現象也可以成為反抗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一項手段(Ong 1987)。那麼,新堯灣這一場落童儀式透露了關於人們的何種訊息呢?
(一)大伯公論述
這一場落童儀式的核心議題在於三月二十九伯公生與劉善邦生日之間的差異,而這差異實係發動於詩巫之砂拉越大伯公運動滲透古晉地方村落的一個片段。對於市況冷落而求變的新堯灣而言,藉參與大伯公運動而附麗於廣大社會,是很容易理解的;然而,坡眾眼中劉善邦這位悲劇英雄卻是全砂拉越幾乎最重要的一位早期歷史人物。於是劉善邦與大伯公之間,頗有矛盾。
對於新堯灣友蘭路坡眾而言,三月廿九日伯公生並不陌生,實際上,同在新堯灣大山下的鎮江亭廣興宮(水口伯公)年度最重要的祭典就是三月二十九日,近年稍稍擴大辦理,花費在5,000馬幣左右;然而,八港門公廟水月宮旁的義文宮(伯公)雖然也在三月二十九日辦理大伯公公祭典,但僅花費不到500元,並非重大祭典;而善德廟更是重來未在三月二十九日辦理任何祭典。
換言之,劉善邦在友蘭路確實被視為伯公,乃至劉大伯與王三伯皆然,然而坡眾並不認為這三位先賢是所謂大伯公。這伯公與大伯公之間的落差,直接表現在祭典日期上,於是總理劉開宗明義問了祭典日期的問題,他說:
弟子摎福首今日來到前,今年三月伯公生…(眾人:二十九)二十九伯公生日,摎劉善邦公作戲,慶祝,唱歌,汝問劉善邦公好麼?厓兜主辦,今年用劉伯伯公介額(總理結巴地),摎佢慶祝。今年厓兜(廟)後背修到恁淨,分劉大伯公…厓兜做福首…(福首黃:合港平安)恁多年無識慶祝,百年來囉。裡下滿弟子、子民、村民恁有心,帣手、出心、出力儕出力,恁仰形講啦喔,伯公劉善邦公來鬧熱看仔,來擲看啊,摎佢擲一下聖筶看啊。
本段言語係整個落童問事的第一個問題,總理劉或許緊張,也或許礙於平素的口語能力,整段話並不流暢。不過,本文認為這段話十足地傳達了眾人的焦慮。首先,三月伯公生的日子總理一時說不出口,賴眾人提醒才覆誦出來;其次,結巴又語焉不詳地用「今年用劉伯伯公介額摎佢慶祝」,字面的意思為「用劉善邦的名義來慶祝」,相當程度地表達了三月二十九應該不是劉善邦的生日,但我們卻已決定用這一天慶祝。
對此,劉大伯倒是態度坦然,立即笑道:「哈哈哈,大聖筶撿來。」當隨即擲出聖筶後,村民的忐忑立即化解,因而滿堂歡欣。然而,劉大伯另有深意:
今年哪…(被眾人話語打斷)…吂,大伯摎汝講,厓擲裡頭下介聖筶,就係嘛分汝兜本年介總理伯福首公來籌備嘛,慶祝鬧熱,幾多夜係汝兜儕介…(再度被打斷)…厓劉大伯,劉大伯公…厓善邦裡廟宮流傳的歷史流傳下來,善邦介生日就係三月初十。
三月初十才出口,眾人立刻焦慮地陷入喃喃自語或討論,並向劉大伯確定三月初十是劉善邦或者劉大伯自己的生日。劉大伯清楚村民的緊張,又說:
過去,厓先講汝兜儕聽,…(總理:下擺弟子無會)…劉善邦介生日係三月初十,三月二十九就係眾神裡介伯公介…(總理:嘸好怪,嘸好閼,弟子就問,今年就來做,下年就三月初十該下來…眾人:三月初十)…汝聽厓講…厓劉大伯真正介哪年生介生日係三月初十。無相關,汝兜儕歷古流傳下來喊伯公介生日,厓講分汝兜儕知,嘸係講出汝兜儕聽,汝兜儕嘸知,無會明白,講出分汝儕明白。下一年愛慶祝也就係哪,三月二十九了,不用顛三倒四了啦,好麼?(眾說:就恁仰,好,好,將就…)
劉大伯既說明三月初十是善邦的生日,但也同意就用三月二十九日就好了,不用搞得顛三倒四。於是只見眾人先是焦慮地安撫劉大伯,到最終高興地接受劉大伯妥協後的安排。如此三月二十九擴大祭典與三月初十劉善邦公生日的歧異,固然化解了,但這仍然引發了兩個問題,其一,往後三月二十九日都要慶祝嗎?村民其實並未如此設想。其二,那三月初十如何辦理?
也因此,第一個問題隨即使福首黃表明:「還就下年(三月二十九)能夠慶祝再慶祝,係講沒斯做兜…沒舞斯沒慶祝就沒慶祝吶」(明年有能力辦理慶祝祭典就辦理,如果沒有就做些…不然就不慶祝了)劉大伯不同意,便說:「該定著係汝兜儕…(被黃打斷)汝兜儕港門輪流總理伯福首公擲聖筶為評來做,嘸係講汝愛想愛理就理無得,臺前擲聖筶為評為準」(意即辦或不辦,要總理福首神前評筶決定)。然而,福首黃的焦慮顯而易見;在劉大伯說話時,立刻打斷:「該斯愛講先麼,摎劉大伯講」(意謂所以我必須先跟劉大伯講明年未必有慶祝儀式)。總理的態度亦然,他說:「劉大伯,下一年介總理還吂知,有裡個能力就能夠做,沒裡個能力就恁仰形過,三牲酒禮一定有啦!」(有能力就做,沒能力就這樣過了,但一定有三牲酒醴),黃又再補充:「沒慶祝恁鬧熱啦!」。此時劉大伯安撫眾人的焦慮:「係沒打緊介」(這是沒關係的)「該經費乜愛汝兜儕去籌備」(經費方面終究也是要靠你們才能籌募到);但兩人仍續表明:「係講大家有提起愛做,就來做,正會同心囉」以及「所以先摎伯公講知啊,…莫怪」。
對話進行至此,村人態度恭敬但主張強勢地表達僅僅今年三月二十九日擴大辦理祭典,明年則未可知。對此,劉大伯仍安撫道:「厓劉大伯來到嘸曉怪汝兜儕」(我劉大伯不會怪你們)。總理仍恭敬地應道:「摎佢講一聲啦喔」(拜託跟劉善邦說一聲好嗎?)總理甚至已忘了,其實在儀式之初,即以擲了聖筶,而且一次成功。而黃則以退為進,怪罪自己:「乜所以嘸知喔,今年吂得問劉大伯喔,所以弟子吂問就先做喔!」(我們不知道[善邦的生日是三月初十]今年未先告知即決定辦理祭典),總理也應和:「講到到就行喔」,黃再說:「講到到就愛行喔,擲忒劉大伯愛問喔,今滿正來問喔。」(竟然討論了就要執行,忘了要先問過劉大伯,現在才來問)。村人的焦慮與劉大伯的安慰成了明顯的對比,而村人則似乎渾然不知。
劉大伯甚至轉而嘉許村民:「汝兜儕,港門汝兜儕頭人伯頷下頭…就做,福首黃:係喔,劉大伯:就係恁仰,就係恁仰喊做誠意」,意謂未經告知便決定執行,是對神明誠意的表現。即便如此,村人似乎並未感受到劉大伯的心意,依舊陷溺在不告而行的自責焦慮中,黃說:
誠意啊…無知厓想講劉大伯會適該怪麼,沒問無得啊,恁多人講愛問啊,無等一下斯劉大伯會適該怪麼,沒來講知喔,啊,摎劉大伯講兜,厓兜關心劉大伯有折?啊…敢愛擲聖筶?
黃仍反覆地講著坡眾不應未經同意便決定在三月二十九擴大辦理祭典,並且自責就算跟伯公先說明難道會對我們自己有折損嗎?隨即請問劉大伯是否需要擲筶告知劉善邦?而總理也立刻附和:「就上下香,摎佢講下啦」。兩人已完全忘記三月二十九日祭典之事早已請示,逕自自責而求解脫。
兩人這段話與劉大伯一番嘉許「誠意」的言語交雜,等同於屢屢打斷劉大伯言語,劉大伯喝了幾口茶,舒緩而堅定地說:
按仰形講話,劉大伯摎汝講,下年介哪,三月介初十日,拜三月初十日就好了,係真真劉大伯介生日…歷世歷代歷古流傳下來就係三月初十日祭拜善邦公。
劉大伯強調劉善邦的生日是三月初十,不能與三月二十九日的伯公生混為一。福首黃原本要告訴劉大伯明年不一定會有擴大祭典,這一點劉大伯先前已答應;但仍只是強調三月初十要祭拜劉善邦。關於日期的問題,最後的對話,福首黃重申因不知善邦生日,也未曾聽善邦言及,而逕選三月二十九日:「汝沒講,弟子嘸知喔…係喔,往擺佢有來就沒講過喔。」劉大伯表示先年曾有遺漏:「厓劉大伯摎汝講識擲忒哪,識漏忒。」黃說:「喔,識漏忒,所以厓裡兜弟子嘸知,就用三月二十九」,劉大伯最後淡淡地回應:「自家知就好了!」。
經此詳細解析以上對話,本文認為2012年4月6日晚上7時這場落童儀式實際上披露了友蘭路坡眾對於三月二十九日擴大祭典的喜悅又不安的雙重情緒,喜悅,因為這是劉善邦廟前所未有的大事;不安,則係劉善邦的生日畢竟不是這一天。二者交雜的結果,則成為集體集慮,並充分表現在儀式的神人交談中。
尚有進者,本文認為這場祭典實係砂拉越大伯公文化運動的漣漪。前一日,當總理、福首與工作人員在水月宮理事會主席與秘書長的主導下,召開行前籌備會,當時秘書長建議的舞臺背板標題為「新堯灣友蘭路善德廟劉善邦大伯公公寶誕千秋文娛晚會」,然而總理與福首們認為應刪去「大伯」兩字,即認為劉善邦並非大伯公。
以詩巫為中心,作為族群論述的大伯公信仰,以祭典節慶、學術與社會菁英、書籍等交互運作,開始轉化各地伯公乃至義山信仰(蔡宗賢2010,徐雨村 2012)。前述新堯灣的水口伯公即已捲入這一論述,其年度伯公生慶典已冠名「大伯公公」,而這一力量正掀動著友蘭路的劉善邦廟。
客家與潮汕漢文化的土地神信仰,隨移民帶入砂拉越後,其性質逐漸轉化。華南水田生產型態的文化下,田頭田尾的伯公具有濃厚的土地言意義;但對幾乎不事農耕的砂拉越華人而言,土地神性格的伯公已全無意義;唯因水患,使得水口伯公則略微繼承了漢文化的土地公信仰的某種形式。同時,以先賢為伯公,則亦係砂拉越華人伯公信仰的特質(王琛發 2012)。
正當大伯公節方興未艾之際,吾人已察覺它在砂拉越華人商業網絡、觀光與社會網絡上的意義與影響力(張維安與張翰璧 2012),當新堯灣坡眾主動或被動地捲入這一文化運動時,自然是喜悅與不安交加。換言之,在那晚籌備會結束之時,友蘭路總理福首恍然思及:「伯公不知喔!」,其實正因為眾人不由自主地捲入大伯公論述時,驚覺這其實不是本地傳統。對於當地人而言,劉善邦是個具體的先賢,可以透過落童與之交涉。
(二)落童:聖俗交渉
近距離參與觀察友蘭路的落童儀式,明確地感受到被附身之靈媒的雙重特質,身為神明之列,村民對之虔敬有加,是俗者對聖者的神聖態度;然而,一旦下凡附身之後,神明一如凡俗之人,村民可得而與之雙向地商談或請求仲裁。落童的成為聖俗交涉的場合,我們得以窺見神人之間虔誠、商議與見證的特質,說明如下。
善德廟落童儀式讓人印象最深刻的並非神聖莊嚴,而是親切與戲謔。神明附體之後,村民隨即送茶、按摩與關心神明之身體健康。村民與神明交談時,神態自若,一如友人問答,並且不斷地相互打斷彼此言語。本次落童最明顯的例子即福首黃與劉大伯的對話,當時劉大伯已同意往後的伯公生將就在三月二十九日辦理,黃立即表明不敢保證明年能否繼續擴大辦理祭典。黃的口語能力極佳,儘管一再代表鄉民自責未先徵得同意便決定擴大辦理祭典的日子,但是態度幾乎只是告知神明而已,並無商量之意。劉大伯則婉轉但堅定地訓示,祭典要總理福首在神前評筶辦理,不可擅自主張;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喊出「誠意!」「誠意!」並無退讓之意。二者之言談雖然針鋒相對,但全無煙硝味,反倒類似親子之間的親切對話。
在落童儀式中,村民之間也不停地對話,而神明則扮演仲裁者的角色。例如對於三月二十九日到底何時擺設祭品之事,有人認為是早晨,但隨即有人提出這時間太早,傍晚時分即可;最後總理覺得還是提早一些較佳,於是決定五點左右福首便應到齊,開始布置。此時劉大伯堅定地說:「汝兜總理伯福首公大家去安排就好了嘛!」使村民達成的協議。
然而,落童儀式的神聖本質仍是顯而易見的。落童只要轉用莊重的言語與神溝通之時,村民立即下跪。例如,當總理請教三月二十九當天儀式如何安排時,落童拿起聖筶,口唸:「本廟邦以下,劉大伯到前,劉善邦、王三伯、玄天上帝、劉珍仙、老祖先師、列位眾神,神明到前,厓劉大伯過來,表達厓劉大伯眾神介意願,本年總理伯福首公三月二十九慶祝善邦到面前,作戲介唱歌,厓劉大伯一口答應」眾人聞聲,隨即跪下。又例如儀式開始之初,眾人對缺席者的指責,明白地顯示對儀式的尊重。又例如,祖父帶著嬰兒大小的孫子前來,請劉大伯庇佑之時,孩子的母親隔幾尺之遙,一再地逗弄著孩子,又雙手合十敬拜,十足顯示了母親真心的信仰態度。
最後,特別值得注意的,這一聖俗交涉的場合,神明既以降臨,只要落童開口,便係神明主觀意志的表達,那麼何以又要藉由「聖箁」卜得神意呢?本文認為這係因為神明與落童畢竟同在一個主體之內,落童口說之言語究竟是神的言語或者凡人的言語,難免引發落童假藉神明之意的批評。同時,就本次儀式而言,問事的主題是劉善邦本人,但降下的卻是劉大伯,因此由劉大伯以聖箁代眾人卜問劉善邦,亦稱合理。因此觀之,友蘭路的落童儀式係以擲筶這一客觀法則,補強了純然的主觀。同時,當落童擲箁之時,他恍神明、靈媒與儀式專家集聖俗於一體,這完成符合儀式中,落童的形象。
總之,落童儀式實係人神之間,乃至村人之間的溝通場合。
五、結論
藉由2012年4月6日晚上一場為了詢問擴大辦理祭典活動的落童儀式,本文發現友蘭路劉善邦廟在捲入砂拉越大伯公族群文化論述之際,充滿著喜悅與不安的雙重情緒。喜悅是因為劉善邦值得,不安則因為劉善邦畢竟不是大伯公。
劉善邦這個曾經攻陷皇宮的客家礦工英雄,在馬來西亞多元種族而政治不平等的局面下,已成為砂拉越客家華人的重要族群象徵,福州人的黃乃裳是詩巫的對照個案,至於國界之外那遠方西加里曼丹的羅芳伯,則是英雄故事的原型。因此,他當然值得大肆慶祝。
可是劉善邦就是劉善邦,不是那個匿名的眾神大伯公。從起乩的落童口中,村人得知善邦的生日是三月初十,而非三月二十九日的大伯公節。對友蘭路坡眾而言,劉善邦確實是伯公,而且無論這一名姓是否在歷史上真有其人,對港門坡眾而言,他就是那位錯失統治砂州的悲劇英雄,而且他以及他那些義結金蘭的弟兄們,還會在某個落童的晚上,與村人互道家常,並且解決個人生命與社區生活中的各式難題。
每一次落童,劉善邦的故事就不知不覺地在這村落上演一次,他一方面解決了庶民最底層的生活吉凶問題;也強化了客家華人的身份認同;當然也不得不承受了社團與地方菁英在這民間信仰裡的縱橫捭闔。
參考書目
Department of Statics, Malaysia,
2011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of Malaysia 2010: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Basic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ng
1987 Spirits of Resistance and
Capitalist Discipline: Factory Women in Malaysi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王琛發
2012 信仰的另一面:從南洋天地會視角解讀大伯公,刊於徐雨村編,族群遷
移與宗教轉化,頁59-91。新竹:清華大學人社院。
余光弘
2000 臺閩地區漢人民間信仰中「上身的」現象初探,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集
刊54: 97-113。
李海豐
2011尋找劉善邦。古晉:砂拉越華人學術研究會。
林富士
2005 醫者或病人:童乩的臺灣社會中的角色與形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集刊 76(3):511-568。
林瑋嬪
2002 〈神的具形化:談漢人的神像與乩童〉,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
所舉辦,「物與物質文化」學術研討會」,6月11-15日,台中縣東勢林場。
徐雨村編
2012 族群遷移與宗教轉化。新竹:清華大學人社院。
張恭啟
1986 多重宇宙觀的分辨與運用:竹北某乩壇問乩過程的分析,中央研究院民
族學研究所集刊61:81-103。
張維安與張翰璧
2012 馬來西亞砂拉越大伯公節意義初探,刊於徐雨村編,族群遷移與宗教轉
化,頁93-117。新竹:清華大學人社院。
嵇童
1983 「童乩研究」的歷史回顧,臺北縣立文化中心季刊37:36-42。
蔡宗賢
2010砂拉越大伯公廟資料彙編。詩巫:永安亭大伯公廟。
落童紀錄
一、請神
接近七點時,幾位福首開始上香,福首李載來「師父」張,總理劉及其他福首也到達並陸續上香。上香之時,眾人發現兩位負責帳務的工作人員未到,他們跟村民朱說自己另有會議,無法前來,偏偏朱又沒來,打了電話又沒接,責怪了頗久(7:00,此為當日晚上時間,下同)。
師父開始請神,總理福首及一位婦女帶著兩個小孩一起合十跈拜。師父請神之時,並未換裝,而以常服進行。先請廟祀諸神,再請四方諸神,最後請開基地地主與四方地主。其次表示今日三月十六日,總理劉福首李(姓名照唸)等謹備祭品(特別提及茶),為三月二十九伯公生千秋聖誕之事,請問伯公旨意。
師父張拿起聖筶,說道總理福首齊齊跪在案前,請三位先人大德(王三伯、劉大伯、善邦公)到前來,聖筶為評(第三次才聖杯)。隨即以秣草水灑淨案座,並且飲一口淨身,準備正式進入落童儀式。
二、落童
師父張穿上紅色麻布袍並綁上頭巾,扮成落童,低頭坐在供桌前,閉目等待伯公附體。靜默之中,兩位福首仍三言兩語地討論著福首朱未來之事,有人表示今夜福首這麼多人,總理也說儀式順利就好,最後決定「莫搭理佢」。靜默持續中,一會兒落童的鼻息聲越來越大,仍有兩人討論著有件事要記得問(7:13)。
落童搥桌、咳嗽、歎息,意謂神已附體。總理關切地問落童:「恁嗽啊!」落童拿起錢製小聖筶擲於桌上,第一次笑筶,落童應聲低笑;第二次還是笑筶,總理對落童說:「笑啊,恁歡喜啊!」第三次終於聖筶了,落童拂髥並沙啞低沉地笑了幾聲,此時神明附體(落童)了!總理問是哪位到前來,請示。落童低聲用氣音說,劉大伯。落童持續咳嗽,鄉人問是不是要食茶,上了茶,總理表示是很香的茶,他去打包(購買)的,弟子沒閒自己去沖(7:16)。
三、問事
(一)祭典日期
總理:劉大伯啊,弟子…(此時劉大伯喝茶);福首黃:等佢食忒。劉大伯:(飲罷)有話當面講(7:18)總理:弟子摎福首今日來到前,今年三月伯公生…(眾人:二十九)二十九伯公生日,摎劉善邦公作戲,慶祝,唱歌,汝問劉善邦公好麼?厓兜主辦,今年用劉伯伯公介額(總理結巴地),摎佢慶祝。今年厓兜(廟)後背修到恁淨,分劉大伯公…厓兜做福首…(福首黃:合港平安)恁多年無識慶祝,百年來囉。裡下滿弟子、子民、村民恁有心,帣手、出心、出力儕出力,恁仰形講啦喔,伯公劉善邦公來鬧熱看仔,來擲看啊,摎佢擲一下聖筶看啊。劉大伯:哈哈哈,大聖筶檢來。總理:好,來來來,大聖筶。(劉大伯起立擲筶,第一次就聖筶),眾人高興的說:聖筶,聖筶聖筶,伯公愛,伯公愛作戲。哈哈哈……劉大伯:今年哪…(話未停,被福首黃打斷。)黃:四夜啊,劉大伯。總理:三月十六,可以…(總理口誤,實係三月二十六。)劉大伯(立刻接口):吂,大伯摎汝講,厓擲裡頭下介聖筶,就係嘛分汝兜本年介總理伯福首公來籌備嘛,慶祝鬧熱,幾多夜係汝兜儕介…(福首黃:厓兜儕愛問嘛,該晡日匆匆忙忙,嘸記得先問劉大伯劉善邦公。劉大伯:喔…厓劉大伯,劉大伯公…厓善邦裡廟宮流傳的歷史流傳下來,善邦介生日就係三月初十…眾人:三月初十(眾人聽說三月初十,提醒要寫下。另外福首李提醒黃,黃隨即追問,是劉善邦,而非劉大伯自己的生日。)劉大伯:傳下來的歷史,歷史…眾人(急著想確定):無係劉大伯,係劉善邦,劉善邦公喔……劉大伯:啊?眾人:係劉善邦公,劉善邦公介生日囉…劉大伯:係囉,初十啊!福首黃:三月初十喔?劉大伯:過去,厓先講汝兜儕聽,…總理:下擺弟子無會…劉大伯:劉善邦介生日係三月初十,三月二十九就係眾神裡介伯公介…眾人:喔…這就係弟子嘸知…,總理:嘸好怪,嘸好ad,弟子就問,今年就來做,下年就三月初十該下來…眾人:三月初十…劉大伯:汝聽厓講…厓劉大伯真正介哪年生介生日係三月初十。無相關,汝兜儕歷古流傳下來喊伯公介生日,厓講分汝兜儕知,嘸係講出汝兜儕聽,汝兜儕嘸知,無會明白,講出分汝儕明白。下一年愛慶祝也就係哪…三月二十九了,不用顛三倒四了啦,好麼?眾說:就恁仰,好,好,將就…
福首黃:還就下年能夠慶祝再慶祝,係講沒斯做兜…沒舞斯沒慶祝就沒慶祝ne(7:23)劉大伯:該定著係汝兜儕…福首黃:該斯愛講先麼,摎劉大伯講。劉大伯:汝兜儕港門輪流總理伯福首公擲聖筶為評來做,嘸係講汝愛想愛理就理無得,臺前擲聖筶為評為準。(背景聲音為福首李跟我借筆記日期及問錄音了嗎?我回答有。)總理:劉大伯,下一年介總理還吂知,有裡個能力就能夠做,沒裡個能力就恁仰形過,三牲酒禮一定有啦,哈…福首黃:沒慶祝恁鬧熱啦!劉大伯:係沒打緊介。總理:係講大家有提起愛做,就來做,正會同心囉!劉大伯:該經費乜愛汝兜儕去籌備。黃:所以先摎伯公講知va,…莫怪。總理:摎佢講一聲啦喔。劉大伯:厓劉大伯來到嘸曉怪汝兜儕…黃:乜所以嘸知喔,今年吂得問劉大伯喔,所以弟子吂問就先做喔,總理:講到到就行喔,福首黃:講到到就愛行喔,擲忒劉大伯愛問喔,今滿正來問喔。劉大伯:汝兜儕,港門汝兜儕頭人伯頷下頭…福首黃:係喔!劉大伯:…就做,福首黃:係喔,劉大伯:就係恁仰,就係恁仰喊做誠意。黃:誠意ha…無知厓想講劉大伯會適該怪麼,劉大伯:…誠意…福首黃:…沒問無得va。劉大伯:誠意…黃:沒問無得va,恁多人講愛問va,無等一下斯劉大伯會適該怪麼,沒來講知喔,啊,摎劉大伯講兜,厓兜關心劉大伯有折?啊…敢愛擲聖筶?(劉大伯有點情緒,喝茶...)總理:就上下香,摎佢講下啦(總理將話題轉回三月初十或三月二十九這一先前已處理好的問題)劉大伯:按仰形講話,劉大伯摎汝講,下年介哪,三月介初十日,拜三月初十日就好了,係真真劉大伯介生日。眾人:就拜三月初十…劉大伯:歷世歷代歷古流傳下來就係三月初十日祭拜善邦公。福首黃:汝沒講,弟子嘸知喔,劉大伯:呵呵呵…福首黃:係喔,往擺佢有來就沒講過喔。劉大伯:喔…厓劉大伯摎汝講識擲忒哪,識漏忒。黃:喔,識漏忒,所以厓裡兜弟子嘸知,就用三月二十九。劉大伯:自家知就好了!福首黃:喔…喔…(7:27)
(二)儀式與祭品
總理:啊…劉大伯ho,該日三月二十九開幕伯公裡,愛用仰形介儀式?劉大伯:(沉默良久)大聖筶檢來,(莊重言語,眾人跪)…本廟邦以下,劉大伯到前,劉善邦、王三伯、玄天上帝、劉珍仙、老祖先師、列位眾神,神明到前,厓劉大伯過來,表達厓劉大伯眾神介意願,本年總理伯福首公三月二十九慶祝善邦到面前,作戲介唱歌,厓劉大伯一口答應,一口答應,呃…(轉頭問總理:麼介時愛開始?總理:三月十六。福首黃與李:廿六,眾人更正三月二十六,總理:農曆三月二十六),劉大伯:三月廿六…福首黃:到三月二十九完夜。總理:盡日,著了。劉大伯:盡日,就係結束了,眾人:係,係。總理:先二十六開始,做四日夜。劉大伯:聖杯表達…(第一筶笑筶,笑啊)三月二十九日盡日結束了,正來慶祝,三牲酒醴…福首黃:三牲酒醴,本成斯有。劉大伯:…壽糕、壽桃、齋儀果盒、篙燈篙燭,厓本廟介裡就係準備裡兜清香好分人奉拜(有有有…背景聲,廟外有人以陸豐腔唸道,三牲酒醴,東來東過,西來西過,南來南過,北來北過…),厓難為來到眾善信士。福首黃:嘸會嘸會。劉大伯:厓劉大伯沒麼介要求了!(又笑筶;立刻再擲,才聖杯)
總理:(復誦)三牲酒醴……每年三月初十愛拜三牲酒醴,二十九介盡日,呃…二十九…二十九裡介…劉大伯:厓劉大伯摎汝講(福首與眾人:將就…),將就了。福首黃:夜市喔?劉大伯:汝兜儕仰般做就仰般來。
總理:劉大伯,裡後背,弟子……(與工人討論施工事後,問劉大伯,但被眾人關於先前儀式用品之事的細節打斷。)(眾人相互討論祭品擺設時間)
福首李:二十九該日me,六點福首全部來放,汝兜早早放,沒人看會掉忒,不得啦,二十九該日。總理:移早五點就開始囉。福首李:不得較早放啦。眾人:五點零,六點啦!劉大伯:(語氣堅定)汝兜總理伯福首公大家去安排就好了嘛!眾人:沒愛朝晨?李克強:沒愛朝晨!眾人:五六點就愛來
(三)寶物
總理:(對大家)還有好事愛問劉大伯麼?福首李:(走上前,意味深長地)這水溝透去,廟唇滿tang下背有麼介寶物沒?(7:34)劉大伯:寶物,有寶物沒?該總理伯有收成啊就好了。福首黃:總理收成就好了。總理:係麼介東西啊?告訴弟子。劉大伯:就係哪,寶物哪,就係奈年奈時介總理伯收成就算了。福首黃:佢講有寶物總理伯收成就好囉,佢講。眾問:麼介寶物?黃:嘸知,佢沒講。
(四)施工
總理:裡伯公後背,該沙…(先對眾人問,後背圍起來好麼?眾人就說汝問佢)劉大伯喔,伯公裡後背,善邦介墓喔,該泥緊來緊少,用紅磚摎佢定起來恁大…好麼?劉大伯:(沉默很久)汝想仰般就仰般(7:36)
總理:沒,沒,有麼介日子麼?麼介時辰麼?有犯到麼介時麼?弟子嘸知啦,做生理喔,弟子還有喊人帣手,有麼介日子啊,沖麼介時,沖麼時啦,有一個法令避走佢啦,分弟子來順順介做……因為弟子做生理,沒仰形介時間抽出來,奈日介時間行行,汝乜知,做揪就做閒,嘸揪就越做越沒。打算用紅磚焗一個…「小小的範圍」(華語)就好。劉大伯:「範圍」係麼介?總理:就一個圈定定。劉大伯:範圍!四月有好日子! 總理:啊?劉大伯:四月,四月就做得做。總理:四月就好了,四月就可以做了,有麼介時辰麼?劉大伯:初三、初七、十七、廿七,有七介日就好了。總理:厓寫起來,有筆麼?(複誦,拿紙筆請黃記下)。總理:分厓符令做護身,好麼?(拿出備用符令紙)劉大伯:檢前來,檢前來。總理:愛幾多張?劉大伯:三張為準。總理:三張黃符麼?(劉大伯畫符)總理:愛印。總理:汝摎佢開下光。(新印章開光,再符開光)劉大伯:龍珠有帶來麼?總理:有(拿出新的紅色印泥)(劉大伯用印,擊掌施法於符令。)總理:三張分佢護身。(拿給施工者)
(五)帣印
劉大伯:還有愛問麼?總理:厓摎汝講聲。(對大眾)還有麼儕愛問麼?村民:厓有,厓有,厓裡啊孫啊介帣吂得印,摎佢點一下(7:43)劉大伯用印在小孩天庭,其父母遠遠逗弄小孩,笑容可掬,又合十敬拜。再做青符,用印開光,擊掌施法,讓祖父攜回。
(六)施工
總理:(與眾人商議後)劉大伯,裡下善邦公介理事會(實際上是新堯灣水月宮理事會)佢兜愛載石尪仔屯裡兜放車仔介,子民來看鬧熱,分佢順順做,像裡兜人像麼介車裡兜,佢恁有心,來贊助,出物出力又出纍(錢),希望裡兜子民後背裡平安,朱牯屯裡兜石尪屯分佢平,車好放,分佢順順去做,理下子民平平安安。毋使麼西囉?(7:46)劉大伯:掃淨就好
(七)舞臺
總理:還有麼好事愛問麼(對眾,沒有再要問事者。)總理:(請劉大伯食酒)盡香喔!劉大伯:盡香!(7:55)總理:該舞臺斯做裡直直喔?劉大伯:可以了啊!總理:劉大伯,裡啊劉善邦介舞臺(總理朝外比畫),置裡位向看,係向裡直直向,崎崎放該正位喔?劉大伯:放在正位。
四、退座
總理:裡下弟子沒麼介事囉,弟子問完了,還有汝麼介事愛交待麼?劉大伯:可貺得來麼?嘗啊層層嘗啊!(示意大家喝酒)福首:(對某人)莫走啊,行等出!(眾人分飲)總理:沒麼介事囉
劉大伯趴向供桌,然後喘了一口氣,狀甚疲勞。脫去紅衣紅帽,師父張:(對某村民)有來喔;村民:恁慢到來。師父張:辭神過火囉(拿紙錢對總理)!總理:裡啊愛燒去啊?劉大伯眾神下虔誠到前來,事喔事務已經已經理好一切囉,汝出來領受金銀財寶(擲小聖筶),丙丁火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