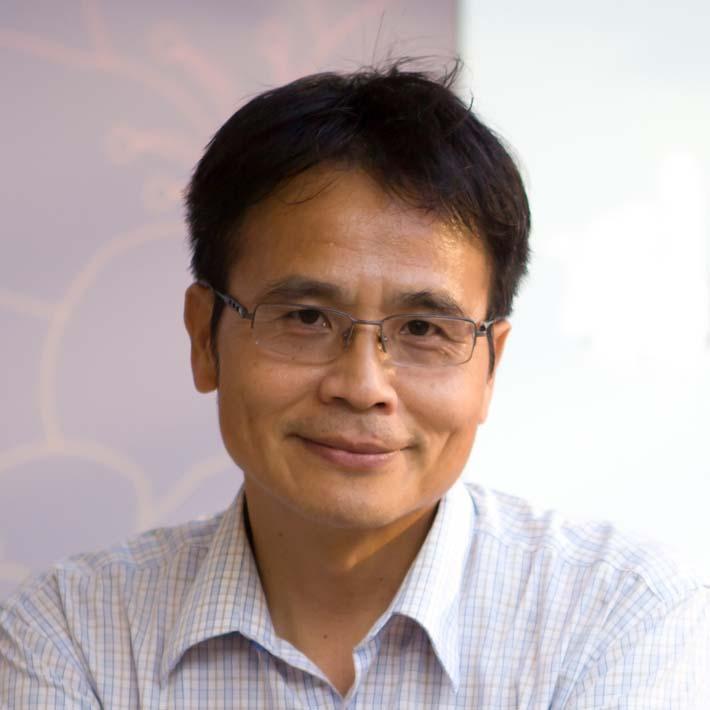初嚐沒有撞牆的臺北富邦馬拉松滋味後,覺得SUB
4似乎不是那麼遙不可及,但它的到來,卻頗意外。
感冒
去年(2013)十二月臺北富邦馬後,經一週休息與恢復,隨即展開新竹城市馬拉松的十六週訓練計畫。這個計畫模式自初馬時便已開始採用,此次由於離比賽僅餘13週,於是我便直接從第四週開始練習。同時,還做了兩項重要調整,其一為以六週上坡跑取代前段之間歇跑;其二為週末的LSD距離不變,但路線全部改為山坡跑。
訓練過程順暢,上坡跑順利地從五趟進步到十趟;LSD山坡跑雖然遇著八九度的陡坡相當辛苦,但也讓我對客雅山與牛埔山十分熟悉。更由於冬季,少了暑熱與汗水,青草湖畔的練習倒像徜徉山水間:
進度是上坡跑,但狀況不好,左膝肌肉有點怪,應該是昨天傍晚才跑過的結果。對我而言,這樣的連續跑應該是有點太過了,所以決定延後訓練。但呼吸了湖邊冷冽的空氣,還轉進了湖心亭,頗有張岱的感覺,也是冬日一得(1/7)。
這真是難忘的冬季長跑經驗,只是萬萬沒想到,就在春天來臨之後,一個週二的下午,感冒像一記重拳直接把我擊倒。賽前一週的週一,早上三節課,中午開會,下午演講,晚上突然發現喉嚨發炎,嗓子啞了。隔天先是外出審案,駕車趕回學校中午會議的車上,已覺全身發冷。接著的演講座談,儘管熱開水一杯接一杯,但已無濟於事。只得傳了簡訊給研究生,取消排定的meeting,直接回家。服了藥,昏睡了一整個晚上。
病來如山倒,幸好病去沒像抽絲。接下來的日子一樣忙碌,而感冒也並未完全痊癒,於是整整兩週沒練跑。比賽當天,騎了機車到達世博臺灣館處的起跑點,仍感倉促。
配速
儘管倉促,但在穩定地執行了既定訓練計畫後,仍有幾點線索,讓我決定大膽地執行四小時的配速計畫。
首先是前三馬跑後的身體狀況,初馬與二馬最後十公里都很狼狽,三馬首次未撞牆,但這三馬跑後幾天都沒有太大的不適,傳說中的「鐵腿」或「鐵全身」都沒發生。我不禁懷疑自己是否最後階段受困於身心狀態,沒能使出全力。
其次是幾項速度指標,800間歇我的水準是3’40”,五公里我已跑進24分以內,甚至我的五分速耐速跑,已經練到16公里。這幾個指標都顯示自己應該有四小時的實力。
最後,本季練習最後幾次的LSD,我採取「31跑」,亦即前3/4慢速,最後1/4配速跑。結果幾次在瀕臨潰散之際,竟然可以再燃體力。我感覺似乎最後十公里有個「切換」按鍵,只要我能按下去,最後就會有奇蹟發生。
五分速
鳴槍之後,擠在起跑線前的我,只比大會時間慢個十多秒,就通過感應紅毯。或許是整整兩週未跑步,加上前兩天大量補充澱粉,毫不費力地就開場了。告訴自己:「前面五公里只是熱身罷了,不必跑太快。」感覺選手不斷往前離去,但自己穩穩地調整氣息前進。忠孝路、光復路、食品路、東山街、公園路,一路都是自己熟悉的老地方,我只是跑著,沒有任何意念。
東大陸橋的下坡處,偶然聽見身旁跑友的手機報速:「現在速度4分48秒」,心想「應該是聽錯了吧!」。接下來經過主辦飯店、百貨公司、護城河、東門城,繞過火車站後,看到第一個里程標示「5公里」,再看自己的指針手錶,才剛過26分鐘。老天,原來剛剛聽到的4分48秒是真的,自己不但沒有慢速熱身,反而超速太多。
接下來仍是簇擁著啦啦隊的市中心,很難靜下心。鄉親們的熱心,讓人不得不心懷感謝地回應,畢竟勞師動眾,管制交通,多所打擾。當然大概也免不了要貌似神勇地輕快向前吧!直到沿著開闊的中正路接近機場時,我終於可以清楚地聽得到自己耳機傳來的180步頻音樂,開始告訴自己就好好面對自己吧!
城市漸行漸遠,繞經機場時,過了十分里。一路上仍不斷地被跑友追過,心情矛盾。真要趕上去,覺得應該沒問題,但是自己明顯地已經超速了。於是冷靜地聽自己的180步頻音樂,一方面任由跑友超越,但也偶爾超越幾個跑友。
海濱路上是15公里補給站,配著香蕉,多喝了水與運動飲料。左側是新竹機場,熱心跑友不斷提醒會有幻象機衝場表演,而且是刻意配合本次活動而舉行的。可惜直到轉入海埔路,仍未見幻象。右轉進入海埔路則讓人愉快,慢車道的路樹與田疇裡,我的音樂變得格外清晰。同時,對向又有折返的人龍,彷彿自己也馬上可以跑到那邊一般。
海埔路的盡頭是港南濱海運河風景區,也是17.5公里水站及感應點。熱心的志工端著水歡迎補給,但是15公里時已補給足夠了,所以婉辭了志工的熱情。踩過感應點時,我竟然只跑了1:32。我的配速策略是以五公里半小時為基準,第一個五公里熱身半小時,之後每五公里要省下兩分鐘,如此在40公里時,我就省下14分鐘,足以應付最後的2.2公里,順利破四。結果此刻賽程不到一半,我竟然已經省下了13分鐘,比預期配速快了8分鐘。以我的水準,這實在快得太離譜了。
折返點
接著便是依舊熟悉的17公里海岸自行車道,第二個折返點在此。去程可能誤以為馬上就要折返,竟覺得有點漫長,幸好回程一下就到了。就在折返點前不遠,瞥見穿著國旗裝的前輩好手,這是他的第65馬。在中正路上他就超過了我,此刻發現自己跟他只差幾百公尺,心情愉悅,而我的半馬僅費時1:51’,剩下的里程只要維持六分速,就足以破四了。
折返之後的17公里海岸線係跑在自行車道上,左側土坡之外,就是大海。假日LSD跑過幾次這路線,駕風巡行於海岸,是不得了的享受。可惜此時視線所囿,感受不到海的景緻。直到接近焚化場時,彎上土丘,才突然看到大海波濤,外地跑友也才發覺自己跑在海岸線邊。可惜也只是這驚鴻一瞥,便又轉回了大道。
隨即經過漁港碼頭處,折向廣大的停車場時,迎面而來的海風,幾絲寒意,提醒了人們冬天離去未遠。這一路我壓低帽緣,穿過貝殻公園的27.5-30這2.5公里時,初次感覺有點辛苦。
五人縱隊
離開漁港與貝殻公園,轉入頭前溪隄岸自行車道,鳥嘴山到鵝公髻山令人賞心悅目的天際線,一列展開,發現自己實在太久沒來南寮了,這真是騎單車與跑步的好地方。踏過30公里的感應點時,費時2:45,比我預期的配速快五分鐘;也表示後半馬的前半段接近自己四小時馬拉松配速的預期。
只是顯然自己開始付出前段配速過快的代價了,便立刻配合著耳畔180步頻的節奏音樂,提前開始採取數呼吸的辦法,告訴自己數到一千吧。原本這一心理技巧我打算35公里後,才開始使用,但是現在卻必須如此。
五百數左右,到達32公里處,馬拉松正式開始了。初馬的狼狽撞牆,二馬仍然撞牆,但狀況略有緩和,三馬克服撞牆,平順完賽。冬季練跑略有體驗:
因應二月少了幾天,跑量不足,又剛好228假期,便把長跑調整到今天,進度是32公里。
第一階段起步狀況很差,十分乏力,跑完牛埔山還差強人意。回到師院時,幾乎沒有再戰十八尖山的意志,於是勉勵自己別怕,仍然賈勇前往。
第二階段的十八尖山倒是比想像中順利很多,但回程的陡下坡已感覺鼠蹊痠麻。
為了達成月跑量300的功課,春節之後,17日內僅兩日休跑,此時,疲勞應該已經累積到頂點了。
回到師院進行第三階段,完全沒有上回31跑的念頭,脫了鞋,赤足又帶點狼狽地跑了兩圈,心想,就輕鬆跑,完成功課就萬幸了。著鞋再戰,一位赤足跑友拯救了我。我本來速度略快於他,但他步頻很好,於是我沒超越他,只是加快步頻,縮小步幅,有點沒禮貌地跟著他跑了三圈。後來他大概煩了,岔出外道,甚至改成逆向跑,但是我卻發生戲劇性變化。不知哪來的力氣,我加快步頻之後,步幅也越來越大,心肺狀況十分順暢,跑完了四公里,心想乾脆再跑兩公里好了。結果油門大開,覺得可以直接跑完八公里。而我也以差不多全馬350的配速,跑完這八公里。最後則用差不多六分速多一些,跑完餘程。月跑量300,搞定了。
為什麼身體有這種力量呢?它藏在哪裡?我本來根本跑不下去的,最後竟然完全點燃。這值得好好思量!
~第13週_長跑(2/28)
這是本季訓練最重要的發現,在極度疲乏的時候,如果點燃體力,就可以燃燒到終點。
再數500次呼吸後,進到35公里補給站,志工大喊「只剩7公里,加油!」。這一段的里程有點亂,補給站是35公里;但出了補給站一小段後,才見35公里的里程指標;再跑一小段卻又見地上的噴漆顯示35公里。偏偏此時自己體力已在搖擺之際,顯得有點難堪。
我的速度已明顯的下降了,應該已低於六分速。我會點燃最後的體力嗎?又該在何時點燃呢?矛盾不安之際,感謝意外出現了「四人列車」。一個年輕跑者,後面筆直地跟著兩位稍長跑者以及一位資深跑者。當他們超越我時,我意識到這就是按下切換鍵的時候了,立刻堅定地踩住180步頻,微微加大步幅,跟跑在這輛列車之後。那畫面真是太神奇了,五人一路縱隊,穩穩地前進,不斷超越一路上的跑者。
進到37.5公里的水站時,帶頭跑者進站喝水,其他人似乎也放慢了。我一來不餓不渴,再來也不想放慢節奏,於是超車持續跑到40公里,才停下來補給。
最後兩公里是段緩上坡,有點折磨人;同時最後這一路又總感覺對里程不太有信心,跑得提心吊膽。直到跑到千甲路上,看到最後800公尺的里程指標,再看著自己的手錶,知道破四已是定局時,才放鬆心情,對著一路的跑友與志工微笑。正巧昔日同事擔任最後路口的指揮者,認出了我,大喊「羅老師加油!」
跑回拱門前,計時器顯示3:57,這數字真讓人高興。太不可思議,真的破四了,而這是我三年前開始跑馬拉松時,認為完全不可能的事。
接受了獎牌,領了大毛巾後,突然開始咳嗽,腰腹頓時抽痛,原來感冒只是趁我跑步時,離開了幾小時,此刻馬上就回來了。
疑問
事後經過計算,前17.5公里我的平均速度是每公里5’17”,亦即一圈400公尺的操場只花2'07"。這當然不算太快,但是這樣的速度跑完之後,還要再跑25公里,對我而言,那就真的太離譜了。中段12.5公里的平均每公里速度是5’47”,已經掉出四小時配速的5’40”。至於最後的12.5公里則是5’58”,亦即勉強撐住六分速而已。
雖然破四,但配速並不理想,也完全不是自己事前所設想的跑法,能破四多少有點運氣。而且,更讓人哭笑不得的是,這次馬拉松很可能距離不足約一公里,因此,我並沒有真的破4,只是接近罷了。
------
繼續閱讀:馬拉松目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