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民間信仰》導論
羅烈師
本書設定主題為「客家民間信仰」,其內涵有兩層次,其一在地方社會的層次上,客家族群民間信仰的自身的特殊性與臺灣漢人的一般性;其二則為族群認同的層次上,民間信仰作為臺灣客家族群論述的一環。其實質對象包含三山國王、媽祖、三官大帝、伯公與義民,以下先以三山國王信仰的族群屬性談起,其次展開地方社會構成原理的討論,最後收攝於義民與族群認同議題。
一、信仰中的族群歷史線索
以民間信仰為進路的客家研究始於歷史學者尹章義,1985年尹章義發表了〈閩粵移民的協和與對立:客屬潮州人開發臺北與新莊三山國王廟的興衰史〉一文,其文以新莊廣福宮廟史為中心,依族譜、老字據與官方檔案等資料,發現了臺北平原的拓墾者並無閩、粵、漳、泉先後之分,亦無平原丘陵之分;拓墾之初的臺北是一個雖有若干個體矛盾衝突,整體而言卻稱得上和睦雜處的墾殖社會。這一各籍移民雜處的情形在清道光年間發生變化:
道光六年今苗栗中港溪一帶閩粵械鬪,十三年桃園一帶閩粵各庄造謠分類,互相殘殺,苗栗銅鑼一帶,靠山粵匪無故焚掠閩莊,公然掠搶,十四年蔓延到八里岔、新莊一帶,閩粵遂展開長達六年的纏鬪,直到道光二十年中,英鴉片戰起,英艦進窺臺灣,臺灣情勢緊急,粵人變賣田業,遷到今桃園、新竹、苗栗一帶的粵人區後才停止。(尹章義 1985)
尹章義把這一段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中,閩粵共同開發臺北,由容忍相安、矛盾衝突到對立血戰的歷史,導致粵人遷離臺北地區的史實,稱為臺灣內部整合運動,也因此名其論文為「協和與對立」。尹文的主要貢獻為勾勒了各祖籍漢人移墾新莊平原的歷史;同時,其文也暗示了臺灣祖籍人群區域分布之態勢,係閩粵械鬥衝突導致的結果。然而,就本書之民間信仰取向而言,其文更大的影響力在於以客屬潮州人(或者潮州客家)與三山國王信仰之關係,拈出族群與民間信仰之關係這一研究議題。
祖籍人群與特定主神信仰之間的關係往往被用來區別人群的重要文化特質,常見的說法是「泉州安溪人信仰清水祖師,同安人信仰保生大帝,汀州人信奉定光古佛,漳州人信仰開漳聖王」。儘管尹文已明示「客屬潮州人」,但是上述特定族群信仰特定主神的觀念,仍引用至客家族群,產生了「客家信仰三山國王」的說法,甚至一度書寫於國民教育的教科書中,這自然是過度解讀乃至誤判的結果,邱彥貴(1993)為此用力甚深。邱彥貴認為三山國王信仰究竟能否作為客家方言群/族群識別的標誌,進而可以追溯其遷徙、融化諸作用,必須討論三個問題:
「三山國王是臺灣客家的特有信仰」的論述完整嗎?
「三山國王是臺灣客家的特有信仰」的命題本身有無需要檢討?
三山國王也是其他區域客家特有的信仰?而第三個問題是基礎,必先完成。(邱彥貴1993)
邱彥貴於是以粵東方志為史料,發現18、19 世紀時,三山國王是主要分布於潮州府全境及惠州府、嘉應州部分地區的地域性信仰,信徒包括福佬和客家兩種,似乎並無方言群/族群的區隔。如果用此信仰去分類臺灣的移民社群,大概僅足以識別移民所來自的地域。換言之,如未深入了解移民的祖籍及祖籍所屬的方言區域,僅憑三山國王信仰是無法辨別一個社區所原屬的方言群/族群。
邱彥貴進一步討論他所提的第一個問題,亦即是否在不同時代的臺灣客家曾以三山國王為主要信仰。研究發現,日治以前文獻充其量只會說三山國王是粵人信仰,然而日治開始官民皆將粵人誤為客人,於是乃有三山國王是客家信仰的說法。至於前述第二個問題,邱彥貴則以非潮汕人群的三山國王信仰,反詰以對。由於漳州即有三山國王廟,吾人理應提問「宜蘭為數眾多的三山國王是否與漳州人群之間有關聯?」而且,宜蘭三山國王有眾多近山防「番」的印象,而這一問題未曾被認真討論過。
這一研究進路不是只為了確認「三山國王是否為客家信仰」而已,重點在於追溯其信仰的遷徙與融化諸作用,隨後陳春聲(1996)的研究即置焦點於臺灣社會轉型與三山國王神格轉變的討論,而這也匯入了神格屬性與漢人地方社會構成法則之討論。
二、祭祀圈與地域社會
「祭祀圈」由日本學者岡田謙提出,定義是「共同奉祀一主祭神的居民所居住的地域」(岡田謙 1960);戰後的研究者以這一概念在中臺灣展開調查研究,還進一步提出「信仰圈」概念(施振民 1973,許嘉明 1978,林美容
1988),成為臺灣漢人社會構成原理法則最重要的理論典範,而這一觀念也幾乎成為常民用語。這一區域性祭祀組織充分表現在臺灣普遍的媽祖信仰中,例如大甲媽 53 庄、梧棲大庄媽 53 庄、大肚頂街媽 53 庄、枋橋頭媽 72 庄、寶斗媽 53 庄、彰化媽三百多庄的信仰圈等。區域性祭典組織外,村庄性、聯庄性、鄉鎮性的媽祖信仰也非常普遍,而本書所選臺灣中部客庄新社之九庄媽祭祀組織即為一例,可以視為是客庄有神無廟之小地區聯庄祭祀的典型,這樣的例子在桃竹苗地區也十分普遍。
這一個祭祀圈是以九庄媽為信仰中心,雖無實質的廟宇,但九庄媽的相關祭祀活動,包括請媽祖、過爐、
出巡、到食水嵙刈香,以及其祭祀費用皆由九庄內輪值的庄頭負擔,有頭家爐主的組織,有巡境的範圍,可說是一個有神無廟的地方性祭祀圈。(林美容、方美玲 2006)
這一進路確認了祭祀圈可以視為民間信仰意義下的空間範圍與界限,然而祭祀圈內是否可以視為一個社群整體(community)呢?同時,形塑這一範圍的還有哪些力量?彼此之間的關係如何?對此,張珣建議「後祭祀圈理論」研究可朝二個方向進行,一為「結構功能理論」,應討論市場、宗族、與村落祭祀三者的共構關係,將祭祀圈擺進社會史脈絡中;二為「文化象徵理論」,視祭祀為權威來源,探討村落與國家官方之間的互動關係(2003:98-100)。
張珣呼籲祭祀圈研究應注意社會史以及官民互動之時,施添福(2001a,
2001b, 2001c, 2004, 2005)琢磨多年後,提出「地域社會」理論,同時也以媽祖信仰個案說明。限於篇幅,本書並未收錄施添福著作,簡說其定義與個案如下:
「地域社會」一詞係指「以一定空間範圍為基礎,建立和維繫人群關係的社會」,或所謂「土親」社會。…街庄民空間…警察官空間…部落民空間,(三者)層次分明,界限清楚,而且統合內疊;既成為國家深入民間、行使權力的管道,亦提供地方人民建立和發展不同層次地域社會的場域(施添福2001c)。
這一定義著重於祭祀圈所指涉的空間範圍,特別是日治之後,國家看起來是這個地域空間範圍的設定者,也是定義者。但是清代苗栗內山地域社會的研究中,國家的重要性消退了,環境與社會本身的重要性則被突顯:
清代的清代的罩蘭埔,一者位居內山,遠離行政中心,國家權力行使薄弱,是典型的邊區;二者所在地點,形勢孤立封閉,水災頻仍,而又族群衝突激烈,是一個環境威脅大的地區……佃首面對國家權力弱,而環境威脅大,為了使墾務順利推展,乃創立「頭家拓墾制」;而頭家則透過「同方言相招」和「同姓相招」的機制,淨化社會的成員,而使罩蘭埔成為客家民系,特別是來自廣東省潮州府饒平縣詹姓一族的天下(施添福2004: 203)。
開闢(雞隆溪流域)之初,(墾民)為了防番聯合設隘;墾地日廣聯合守隘的區域也日益擴大……咸豐年間以降,後龍溪頻發的水災,卻使東西兩岸的居民為了築隄而陷入嚴重的紛爭和對抗。西岸居民在長期動員對抗過程中,不但逐漸彌平內部分裂的傷痕,同時孕育了生死與共的鄉黨感情……促使五庄人聯合建廟和北港進香,以具體行動展現「芎中七石隆興」是「五庄一宮人」的區域意識(施添福 2005:239)。。
換言之,苗栗這兩例顯示,村落基於外在環境危機的利害得失而相互聯結,使村落社會逐漸趨向區域化,成為一個地域社會。至於地域社會之「地域化」是如何達成的呢?施添福的論點與人類學界之宗族與祭祀圈研究成果相同,亦即蒸嘗、神明會及公廟等,扮演了凝聚人群的角色。施添福這一模式是個貫時性分析架構,始於生態環境,終於象徵,而通貫其間的是跨村落的地域認同。在一特定生態區域內的生產模式所塑造的團體認同本來應該是施添福地域社會模式的核心概念,但是施添福顯然更重視形成這一意識的歷史地理因素。下兩節分別以媽祖信仰、民間道壇以及三官─伯公信仰,說明地域認同的內外在面向。
三、跨界與認同
施添福討論無多的認同意識,林美容在新社九庄媽信仰已略略提及,九庄媽在地方拓墾的歷史記憶中,海神形象轉型為山區水神,成為形構「新社地方」的精神動力,也成為地方文化發展的根基。對於這一文化象徵理路的討論[1],林秀幸(2003,
2008)用力最深。
林秀幸認為客庄的媽祖婆進香儀式是向外學習的,因此她以行動者的視角、主觀的感受與認知來詮釋媽祖婆信仰如何被「採用」與
「納進」的過程。關於客庄媽祖信仰的觀察,一如林美容,林秀幸認為客庄一年之宗教祭儀,以上、中、下元,以及春祭和秋祭為經緯而構成,春祭和秋祭與農作期有較直接的關係,開春是一年中農人難得清閒的時節,趁此機會酬神演戲、娛神娛人,所以將媽祖納入當地的慶典活動,其別名就是「春祭」。然而,林秀幸比林美容走得遠一些,試圖詮釋這種配合年俗的現象。苗栗大湖的媽祖祭典活動定名為「媽子戲」而非「繞境」,因此媽子戲在某種程度上是此客庄人為了「鬧熱」緣故而同意舉辦的。此地客庄地方廟宇內的神明除了聖母之外,每一位神祇都是鎮守、穩定、不動如山的形象,因此客庄信仰的流動性應該始自對
「媽祖」的信奉,這樣的「流動」的「價值」和「意義」逐漸地被接受。
進香過程中,香灰與香旗等聖物出了廟門就由廟裡的「部分」轉變成旅途中的「整體」,代表村落與另一個「整體」北港的媽祖廟進行交會、理解和溝通。所有的聖物經由越過每一個爐的手續而連結了一次這個「整體」,進香成員再帶回這個
「整體」的感知、經驗、象徵,重新循線回到自身所在,回到自身的「整體」的倫理,完成進香旅程。也因此,村落年復一年跨越界線與他者相會,理解了自我,也創造了認同。
相對於林秀幸的思路是異質文化的跨界交流,李豐楙(1998)的進路幾乎完全相反,〈臺灣中部紅頭司與客屬聚落的醮儀行事〉一文的主要討論對象是臺中、彰化與雲林的三個紅頭司道壇,三個道壇與特定聚落保持密切關係。田家威振壇系統與西螺二崙港尾一帶25個村落關係密切,這些村落大致上都是已經福佬化的福建漳州詔安客家。蔡家鎮興壇系統的主要執業地理範圍則是埔心、永靖、田尾、溪湖、埤頭與竹塘等,這些聚落也有大量的廣東潮州饒平客家;曾家廣應壇系統則是豐原地區的廣東潮州大埔客家。三個紅頭司道壇系統皆屬正一派,其行業圈與客屬聚落分布範圍大致相合,這是因為道士與地方社會有相同祖籍,而且長期維持密切關係。道士日常為聚落家戶執行補運等小型儀式,遇有建醮等大週期性祭典,則調集同系統道壇人手辦理。正一派道士與鄉民有相同的宇宙觀,於是這些客仔師可以擔任鄉民祈求與重建超自然秩序的中介身份。即使這些聚落已經福佬化,傳統語言已消失,但是信仰習俗反而韌性地保存下來。
四、深層信仰
前文林美容(2006)與林秀幸(2003, 2008)都注意到外來神明(媽祖)信仰與社區內固有年節習俗的配合,羅烈師(2010,2018)也在苗栗銅鑼與西湖觀察到一樣的現象。關於與年節習俗的配合,重點不是時間的巧合,重點在於內在於社區的信仰生活法則,而這一法則即是配合上元與下元之「天公─伯公」信仰的許福還福儀式。
「天公─伯公」信仰體制係建立在小農水田生產模式上,數戶擁有小塊田園的自耕農組成的散村聚落共同祭祀一座伯公;同一灌溉系統內的聚落群以三官大帝(天公)為主神,臨時搭建簡易祭壇,以「爐主與首事」身份,輪值辦理許福還福儀式。伯公信仰所標誌的跨家戶聚落可以視為傳統地方社會的最小單位,三官大帝信仰則在其上,以水利灌溉系統所構成的村落範圍,輪值辦理許福還福儀式,從而建立了這種「天公─伯公」的緊密關係。這種緊密關係如前所述,既可能被視為伯公信仰,而使得伯公成為福神;也可能被當成三官大帝信仰,而被研究者認為三官大帝與灌溉之間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例如田金昌 2005、賴廷奇 2008、傅寶玉2011等)。這一儀式的本質是許福與還福,而福神即為天公伯(三官大帝之賜福天官),伯公則接受聚落群的託付,轉奏三官乃至玉皇大帝。因此,聚落伯公信仰成為家戶以上,人群整合的最小基本單位。從象徵的角度觀察,祭壇天地案之地案上,香桶內的每一支伯公牌指涉著一個特定小聚落;而天案上的天神爐則代表社區。對於這些聚落群而言,由於社群(community)與空間係不可區分的,因此社群也包含了地方(locality),二者相同地不可區分。亦即人與人的關係(社群)係建立在與土地的共同關係上(地方),同時依傳統言語,這是一個天地人三合一的格局。
伯公廟代表最小的基本聚落單位(自然村為典型),幾座伯公廟所聯合奉祀無廟的天公爐則代表村落或村以下的聚落群(行政村為典型)。聯合幾個行政村則會形成地方公廟,其主神可以是關帝、媽祖、三山國王或五穀農神等,但是其年度祭儀往往仍以許福還福為最盛大儀式,主神千秋聖誕則居次。當然這一層級的地方公廟如果就是三官大帝,也十分順理成章,桃園新竹兩縣這種現象最為普遍。
范明煥以傳統文獻說明三官大帝之淵源,再以田野調查所見,描述此一信仰在常民生活中相關的儀式、組織及空間安排,大致上呈現了臺灣客庄三官大帝信仰的面貌。然而,范文的重點在於解釋三官大帝主廟的分布趨勢,全臺計有80餘座三官大帝廟宇,而桃竹苗佔了一半,反之,六堆地區則無,為何如此呢?范文以族群關係為論點,主張三官信仰易為客家與平埔跨族群拓墾團隊接受,因此廣泛建廟。然而,此一主張必先舉證桃竹以外之客庄並無跨族群拓墾團隊,方能證成。其他可能的原因至少包含移民祖籍、獨立歷史事件影響或地區性傳播採借等,可待深究。辜且不論其發生學上的原因,對本書而言,在「天公─伯公」信仰的普同架構下,以三官大帝為主神,在桃竹地區大量建廟,是可以理解的。
洪馨蘭(2013)〈「社官」信仰在廣東蕉嶺與臺灣美濃的比較研究〉一文著眼於確認社官信仰之神格屬性,依文獻記錄,里社真官應是明初即存在之官方性質的鄉里層級社稷之神,而全臺唯三的「里社真官壇」都位於高雄美濃。作者前往移民原鄉廣東蕉嶺縣進行實地田野調查,發現位於蕉嶺之社官,似受盛行當地公王崇拜影響,成為兼司管理水鬼(水域)與陽間官場政治的「公王╱社官」混合體,並呈現出在具威脅之水域邊設壇的區位特性。這個合成的信仰文化於清初被帶到臺灣美濃,又再被移墾社會新設的大量土地伯公信仰所吸納,逐漸變成「伯公化的」「公王╱社官」合成文化。洪馨蘭認為經由這一回溯研究中,重新「發現」了地方歷史。社官在移民原鄉的傳統已有官方與地方文化交融的現象,再傳至臺灣客家地區,又與盛行之土地伯公信仰出現文化會遇(encounter)現象。洪馨蘭確實解決了美濃社官信仰的神格屬性問題,不過,就本書而言,里社真官與王公信仰合成,又再被吸納進伯公信仰,正好顯示本節所強調「天公─伯公」信仰結構的簡潔與力量。天地人格局提供了一個架構,本來就是土地神性質的官方社稷信仰,會被地方定位為類似伯公的神格,是可以理解的。
五、地方社會、族群與國家
選文至此,皆以地方社會為視野,討論民間信仰與客家之關係,賴玉玲(2002)即以地方社會為焦點,描述1998年桃園之楊梅聯庄輪值辦理義民祭典的方式。此一運作方式在以家族為要角,在總正爐主陳泰春主持下,一方面29個地方家族用「公號」之名,擔任爐主、四柱、緣首,組成祭典委員會,共同策畫及執行祭典;另一方面,聯庄區域內施行領調和奉飯辦法,號召家戶參與,還有地方社團配合祭典推行義民節活動。這些組織、制度與活動所構成的動員機制,使得枋寮義民廟的義民信仰得以跨區域傳播,從而構成楊梅庄地方社會。
賴玉玲所指係15年一輪之地方社會運作機制,實際上此一機制係建立前節所討論之三官大帝為主神的地方公廟之上;同時,此一研究成果更意謂著15個聯庄之間,在同一信仰組織架構內,想互學習與競爭,從而凝聚了聯庄內部的社群意識。尚有進者,羅烈師(2006b)以綰合宗教與社會聖俗兩體系的階序體系,說明15聯庄龐大的信仰體系之整合。
枋寮義民信仰創造了一個包含神位、祿位與調位的階序體系,這一體系以義民神位為核心,將捐施與經理廟產有功者的祿位與祭典區內所有信徒的調位收納為一。這個體系的原動力是竹塹城外居民無主的恐慌,而決定階序高低的因素是財產的捐施與管理,但是國家卻因其封神的權力高坐頂端,也因此將信仰帶來族群的異音。
所謂族群的異音係指義民信仰向來與族群議題息息相關,部份閩南社區甚至視義民廟為「客人廟」。然而,實際上林爽文事件後,乾隆皇帝頒了四塊匾額,分別是泉州之旌義、漳州人的思義、廣東入的褒忠與平埔的效順;而且儘管褒忠亭香火最盛,但雲林亦有頗負盛名的旌義亭。然而,早在十九世紀中期時,竹塹地區的義民論述與粵人論述已相互結合,互為表裡,塑造了粵人保莊衛國的忠義形象,因而在臺灣的人群中,明確地區分出「粵人」這一身份認同的族群(羅烈師 2006:255-274)。隨後一百年,粵人身份認同輾轉成為客家認同,而義民信仰也與客家的關係也由之密不可分。1988臺北發生還我母語大遊行,那年正是枋寮褒忠義民廟二百週年廟慶,大臺北地區開辦義民祭(嘉年華)祭典活動,迄今30年,義民信仰已成臺灣客家最重要的族群象徵。
六、結語:地方社會與族群
本書以三山國王、媽祖、三官大帝、土地公及義民爺等主神信仰為主要範圍,從地方社會與族群兩個層次,討論臺灣客家信仰的特殊性。在地方社會的層次,正如所收錄兩篇與引述一篇共三篇媽祖相關研究,三位作者皆知其個案為客家,但全文未及客家論述,因此,一個以全島為範圍的媽祖信仰文化交流現象,是跨越族群而普同於臺灣漢人社會的。然而,這些無廟或陪祀媽祖之祭典係鑲嵌於其地方主神及更深層的「伯公─天公」信仰儀式生活,吾人可以察知客家所獨鍾之宇宙觀。
在族群層次,三山國王與義民本來都不是客家獨有之信仰,也不是所有客家人的信仰,然而都曾某種程度地被冠上客家信仰的標誌。經過研究者之爬梳三山國王之被誤為客家信仰已大致釐清;然而,義民爺作為客家信仰則在臺灣特定的族群區位下,在真實的生活中,持續被塑造與強化。
本書以民間信仰為範圍,惟礙於篇幅,其他普同於臺灣漢人社會,但是客家有其特殊性的恩主公或觀音等信仰,未能納入;儀式層面的醮典或者還老愿之類的習俗,也觸及無多,難免遺珠之憾。最後是都會化與跨華人生活區域的比較方面,前者之社會轉型及人口流向都市的現象,實際上已完全改變客家生活樣貌,其信仰的地域性(locality)與社群性(community)已全然鬆動,研究者必須改絃更張;後者則涉及截然不同的生態、產業、族群與國族等外環境,必定是臺灣客家研究的他山之石。
參考書目
尹章義,1985,〈閩粵移民的協和與對立-以客屬潮州人開發臺北及新莊三山國王廟為中心所做的研究〉,《臺北文獻》,第七十四期,頁1-27。
李豐楙,1998,〈臺灣中部紅頭司與客屬聚落的醮儀行事〉。刊於《臺灣文獻》,第49卷第4期,頁187-206。
岡田謙,1960[1938],〈臺灣北部村落之祭祀範圍〉,刊於《臺北文物》,第9卷第4期,頁14-29。
林美容,1988,〈由祭祀圈到信仰圈:台灣民間社會的地域構成與發展〉,刊於《第三屆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張炎憲編。
林美容、方美玲,2006,〈台中縣新社鄉九庄媽的信仰型態〉。刊於林美容,《媽祖信仰與臺灣社會》,頁291-326。
邱彥貴,1993,〈粵東三山國王信仰的分布與信仰的族群:從三山國王是台灣客屬的特有信仰論起〉,刊於《東方宗教研究》,第3期,頁107+109-146。
施振民,1973,〈祭祀圈與社會組織:彰化平原聚落發展模式的探討〉,刊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36期,頁191-208。
洪馨蘭,2013,〈「社官」信仰在廣東蕉嶺與臺灣美濃的比較研究〉。刊於《民俗曲藝》,第180期,頁83 – 130。
范明煥,2005,〈臺灣客家三官大帝信仰文化〉,刊於《臺灣史學雜誌》,第1期,頁67-91。
張珣,2003,〈打破圈圈:從「祭祀圈」到「後祭祀圈」〉,刊於張珣、江燦騰主編,《研究典範的追尋 : 臺灣本土宗教研究的新視野和新思維》,頁64-107。臺北市:南天。
許嘉明,1978,〈祭祀圈之於居臺漢人社會的獨特性〉。刊於《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1卷第6期,頁59-68。
陳春聲,1996,〈三山國王信仰與台灣移民社會〉。刊於《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80期,頁61-114。
賴玉玲,2002,〈楊梅的義民信仰聯庄與祭典〉。刊於《民俗曲藝》,第137期, 頁165-202
羅烈師,2006a,〈臺灣客家之形成:以竹塹地區為核心的觀察〉。清大人類所博士論文。
--------,2006b,〈臺灣枋寮義民廟階序體系之形成〉。刊於《客家研究》,第1期,頁97-145。
--------,2010,〈階序下的交陪:一個客家地區的媽祖信仰〉。刊於莊英章、簡美玲編《客家的形成與變遷》,頁301-335。新竹:交通大學。
羅烈師、邱曉燕,2018,〈社群與地方:伯公信仰與北臺灣傳統社會之構成〉。刊於徐雨村、張維安與羅烈師編,《土地神信仰的跨國比較研究:歷史、族群、節慶與文化遺產》,頁91-110。苗栗三灣:桂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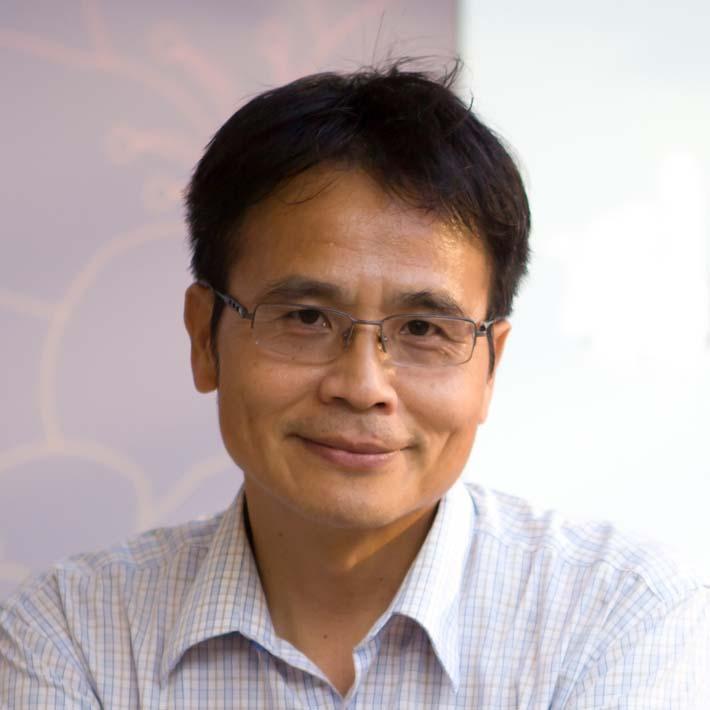

0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