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9日 星期二,上午8:30
沒頭祖公:羅華酉魂斷下橫坑之謎(1806-1821)
羅烈師
交大客院
(刊於《新竹文獻》,67:24-31;2017)
十五世祖 華酉公 生乾隆四十八年,卒嘉慶廿三年,享年三十六歲。誕生於廣東陸豐縣河田,十六歲時隨父渡台,開墾於于下橫坑,不幸遭蕃害而亡,聚妻范氏,無生男,嫁出無傳,立華業公之第三男雲清為嗣。
羅華五 1859
沒頭祖公
羅華酉(1783-1818),我來臺祖鵬申公(1757-1837)的長子,[1]16歲隨父親移民臺灣,廿年後在關西下橫坑墾耕時,在一場客家與原住民衝突中身亡,那一年是嘉慶23年(1818)。從小聽阿公說「頭擺仔來臺祖在下橫坑開墾,華酉公介頭林分『蕃仔』剁忒,正會徙去汶水坑。」[2],幾分驚恐,也許多不解。為什麼會去下橫坑?人是誰殺的?為什麼要殺人?這幾年接觸了許多古文書,對新竹史的理解日益加深,慢慢地解開了這些謎團。
飛鳳山
對於童稚居住湖口的我而言,新竹所知有限,關西就是個內山鄉鎮,而祖先死難的下橫坑又必定在深山與原住民接壤處。等到關心新竹歷史,翻開老地圖後,才驚覺下橫坑根本不遠。其實向北翻過鳳山溪,新埔街在不遠處;向南越過飛鳳山,就是芎林。至此不禁疑問,下橫坑會這麼危險嗎?
下橫坑位於關西鎮最西側,今稱新力里,在清治末期至日治初期,為下橫坑庄,西北邊及北邊凸出部分西側與下南片庄(關西南和里)為鄰,北邊凸出部分東側及東北邊以鳳山溪支流下橫坑溪及丘陵地與坪林庄(今屬關西上林里)為界,東與上橫坑庄(今亦屬關西上林里)為鄰,南邊為王爺坑庄(芎林鄉永興村)為界,西邊為中坑庄、水坑庄(芎林中坑村與水坑村)。
下橫坑依客語字面之意即靠下游的橫向溪流,其東面有上橫坑,二者皆注入縱向的鳳山溪。下橫坑上游有下橫坑山,海拔470公尺,係分水嶺,也是關西芎林兩鄉鎮之界山。飛鳳山丘陵是關西西南方之等腰三角形狀丘陵,底邊為關西、九讚頭線,頂點為台地西北端之犁頭山;底邊長約九公里,兩邊各長14公里,面積約60平方公里。鳳山溪灌流於丘陵北緣,頭前溪灌流於其西南緣,兩溪均形成廣大的沖積河床,呈網狀流路,兩側的沖積平原在犁頭山附近會合,兩溪下游並形成廣大的新竹沖積平原,是絕佳的水稻耕作區。本丘陵頂部平坦,面上留有台地礫層蓋覆,大部分高度300公尺以下,向西緩傾,西北端高度降至海拔40公尺左右。飛鳳山塊高度在470公尺以下;原地形已被燥坑、鹿寮坑、王爺坑、倒別林坑等溪切割。這南北兩向支流沿岸零碎的河谷小平地,就成了漢移民開墾水田的安身立命的小天地。
侵墾
鵬申年逾不惑方於1798年攜妻及三個兒子遷臺,在現今苗栗縣中港溪上岸;來臺之後前幾年之行止已不可考,最早出現的記載就是羅華酉於1818年命喪下橫坑。關於漢人侵墾下橫坑的歷史,《渡臺記》(何明勳 2015:19)有一筆珍貴的見聞:
六家莊至下橫坑,乾隆乙巳已墾成,倒縛牛至鹿寮坑,只墾坑口未墾山,賽夏族番不肯退,[3]集結盤據飛鳳山,北山頭至南山凸,盤旋山林出草繁。
這段紀錄顯示,漢人係沿頭前溪與鳳山溪向東擴張耕地,並沿兩溪支流上攀低矮丘陵。起初先開墾坑口,亦即支流匯入主流之小沖積扇;然後才逐步進山。拓墾事業最大的阻力除了地形以外,就是不願放棄獵場的原住民。乾隆乙巳年即1785年,漢人已沿下橫坑溪墾成下橫坑沿岸農田;而從倒縛牛至鹿寮坑則僅及坑口。這段見聞對漢人侵墾歷程的描述應該沒有問題,但是拓墾時間恐怕須要商榷。嘉慶11年8月竹塹社通事荖萊湘江等所立之〈嘉慶十一年八月老古石竹塹社通事荖萊湘江土目衛福星等立給總墾批字〉(張炎憲等1993:109-110)是較可信的線索,引述說明如下:
立給總墾批字竹塹社通事荖萊湘江、土目衛福星、番差、甲首、耆番等,承祖父遺有樹林青埔一處,東至上橫坑水為界,西至下橫坑西坑水為界,北至枋寮溪水為界,南至九芎林分水為界;四址面踏分明,坐落土名老古石。
本總墾批字由通事、土目及番眾代表等給出,土地座落東西以上橫坑溪、與下橫坑溪為界,南北則分別為飛鳳山脈分水嶺與鳳山溪,舊地名為已消失之「老古石」,大致上包含上橫坑與下橫坑兩處。
今因洋匪滋擾,各憲調撥社番隨軍前往,各番家眷日食,系通土代借,費用無征,無奈同番耆、甲首等商議,願將老古石埔地給與漢人江顯為、吳圓叔、林胡官等承墾,前去自備工本、牛隻、種子、農具、糧食開坡鑿圳,墾成水田,帶大溪圳水,任佃上下築坡,開圳分汴,通流灌溉。
竹塹社人同意將老古石土地讓漢人江顯為等人承墾為水田,而促成簽署此墾批的原因係為籌措社人家眷日食,而這又是因為竹塹社青壯被政府調撥隨軍備戰;至於洋匪滋擾,應該指的是嘉慶11年的蔡牽之亂。
墾成之日,丈明甲聲。其丈篙號式系一丈四尺五寸為一篙,周圍二十五篙為一甲,照台定例。其埔自丙寅年起,至丙子年止,並無供納大租。丁丑年以來,水田按甲供納大租榖,每甲供納大租榖六石;其園遞年早季照台例一九抽的,永為定例,日後不得加減。
待水田墾成之後,墾戶須向社人繳納大租,每甲定額租六石,旱田則抽10%收成。只是從丙寅至丙子(1806-1816)十年間不納,1817之間才開始繳納。
其業意欲別創,任佃退賣,業主不得阻擋。此租業係眾社番公同合約,願與湘江、福星收租,永為己業。其大租粟務要風扇精燥,送至業主倉前交納,不得少欠,即給完單,付佃執照。保此租業並無來歷不明;若有不明以及番耆人等生端滋事,係通土同番差、甲首等一力抵擋,不干承墾之事。此系二比甘願,兩無迫勒,恐口無憑,立合給總墾批字一紙,付執為照。
批明:眾番出給上下崁老古石青地埔一處,與漢人開墾,十年為期,並無供納租榖。丁丑年以外,水田按甲供納,每甲納租六石,永為定例,日後不得加減,批照。
嘉慶十一年八月日 竹塹社七房眾番合給總墾批字[4]
這是個十年的約定,這十年間竹塹社人收不到大租,純就墾批而言,看不出社人有何立即與直接之收益;讀完通篇,驚訝地發現社人甚至不會因為簽出這紙墾批而拿到任何現金,令人不解此墾批對竹塹社人之生計有何直接而立即之幫助。簡言之,這顯然是個不公平的契約。既然如此,為什麼會簽署這樣的合約呢?一般人可能直接訴諸漢奸番憨這一刻板印象。我倒認為尚有其他可能。
表面上這墾批的立約標的是拓墾權利,竹塹社人係將土地拓墾權交給漢人;然而,這樣的交付背後卻是通土(亦即通事老萊湘江與土目衛福星)由竹塹社七房眾人手上,取得老古石土地的所有權;因此合約上才會有「此租業係眾社番公同合約,願與湘江、福星收租,永為己業。」那麼社眾為什麼甘願把這所有權交給通土呢?那是因為青壯社人隨軍作戰的情況下,通土有責任(也可能承諾了或者實際上也實踐了)負擔番眾生活,而這也就是合約表明「各番家眷日食,系通土代借」之故,而其交換條件即番眾將原本公同合約的土地,轉為通土的個人產業(己業)。這就樣,社眾不小心也可能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跨過了土地所有權的不歸點,這塊土地從不能買賣的社眾公同產業,轉換為通土的個人產業,甚至後來就由通土自由買賣。於是土地所有權就產生了急遽的變化,而且這樣的現象早在一甲子或更早以前就已發生,平埔社群在各地失去土地的模式,大抵皆是如此。[5]
這正是漢人侵墾下橫坑的開始,我推估羅鵬申與長子羅華酉等一家,就是在這紙墾批之後,直接參與開墾工作的墾佃。這不平等的合約意謂著極高的風險,而極高的風險來自其他原住民。其實竹塹社眾並沒有權力轉讓乃至出賣這塊土地,因為他們並未徵得泰雅賽夏等原住民的同意,於是衝突就不可避免了。
隘防
下橫坑口距離新埔街上不過六七公里,從坑口到下橫坑中游最開闊平坦處也不過一公里左右,一個飛鳳山北麓中段的村落,會有多危險?如何會被「出草」?然而族譜紀錄的事實擺在眼前,嘉慶23年(1818)羅華酉就是死於下橫坑,為什麼會這樣呢?這樣的疑問,只是用當代新埔與關西思考十九世紀初的鳳山溪流域罷了,下橫坑與其所在之飛鳳山丘陵的危險,在古文書裡歷歷在目。嘉慶25年九鑽頭[6]等庄與陳福成(長順)墾號約定之設隘總契(吳學明
1998:159-161)正因此而簽署:
同立總契字人九鑽頭莊、山猪湖、猴洞、十股林、石壁潭、水坑、及南河、燥坑、上下橫坑;山猪湖洞墾戶劉引源、新興莊墾戶衛壽宗等,為生番猖獗,時常出沒,沿處擾害,各莊佃人王會三、曾保生、李秉賢、黃青蘭等會同各莊籌議,欲在於南河山坑建設隘寮三座,堵禦兇番,使各所耕佃無慮番。
飛鳳山丘陵東、南與西北十庄代表與劉引源墾戶及竹塹社衛壽宗墾戶等,苦於「生番」猖獗,時常出沒,沿處擾害,於是想在丘陵東側最接近泰雅領域的南河山坑新設三座隘寮,以保漢人平安。然而,原本設置之隘防人力就已欠缺經費,現在又要新設隘寮,只得開發新財源,於是找來閩人陳長順:
但礙隘糧無著,仍又起蓋隘寮,一切需費難以籌辦,爰集眾莊籌議,歸與陳長順出首承辦。議將南河內及九鑽頭起,至水坑、下橫坑止,即就該地各處尚有未墾餘埔,併及山林,即日當眾踏界,東至內石山門後,由南河從小北河溪直透為界;西自水坑赤柯崙,透中坑內為界;南從山猪湖隘後嵌眉蔭溝,透猴洞背石碧潭坑口連水口各為界;北由大北河及燥坑,透上下橫坑口各與溪令水為界;四至界址會眾公同踏明。至等處樹林荒埔等各另立定界書約,情願概歸陳長順自備工本,招佃開闢,繪具確圖,逐一注說呈繳,永為己業。
陳長順當然不會平白花錢為粵人與竹塹社人守隘,交換的條件就是將簽署各庄尚有未開墾之埔地,讓給陳長順自備工本,另行招佃人開墾,並且繪圖註記經眾人確認後,永為成為陳長順的產業。簽署人劉引源等隨即呈報淡水廳同知,請求同意此一轉讓;陳長順便即建造隘寮,募集兵丁,開始防衛安全。同時本區域內之墾戶、通事與土目等,也就此宣告先前已有的墾約一律作廢,即使原本擁有墾權卻未墾之人,如要在區內開墾,也必須徵得陳長順同意,並且依規定繳納應分擔的守隘費用:
源等即於本年九月二十四日,呈請淡防分府准歸順墾戶自行招佃,就地墾耕,以資隘糧,並起蓋隘寮,募丁勇防守,可保附山居民毋致番害。經據各墾戶通土呈請,即將前墾同為廢紙,無論前墾之人欲行該地墾種,另向墾戶長順承給,酌貼隘費,不敢違約。
當下即約定,新進佃人前來開墾者,應以收成的5%作為隘防之分攤費用;尚有進者,也決定各庄議定數額,共同分攤原有31名隘丁薪資,而且全部撥入新設隘防,由陳長順調度:
即日當同商議,所有佃人欲該地耕種以及等項,議訂一九五抽的,以資隘費外,年需口糧不敷,按照各戶議貼,各立合約為據。其燥坑貼隘一名,上橫坑貼隘四名,下橫坑貼隘三名,山猪湖、猴洞貼隘十名,十股林貼隘三名,所有石壁潭隘丁十名,稟請改撥入新隘協防,所需口糧即就各莊按月照舊支給,不得推諉,亦不得違約。
於是陳長順付出五百大圓取得區內全部未墾土地之所有權,同時接下了全區隘防經費管理與防務。
保此各處該地係源等前年向各社番承給,與他人無干,並無干墾戶之事。此係二比甘願,各無反悔,口恐無憑,同立總契約字一紙,付執為照。
即日批明:陳長順自備出歸管工本銀五百大員正,當眾公同交源等各親收足訖,批照。
嘉慶二十五年十月 日[7]
這一紙1820年的隘防約定,當然是斷送幾條人命後,粵、平埔與閩人不得不然的因應措施,實際上嘉慶二十年(1815)猴洞庄就已發生了重大衝突,古文書的紀錄是:「…不料嘉慶乙亥年間,突遭生番出擾戕害,莊散民離,地方荒蕪」(吳學明 1998:175),而羅華酉之死,就是這些散見史料中可見未見死難者之一斑。然而,就像前段所分析,我們這些歷史讀者應該同時領悟,這契約與嘉慶11年老古石給墾字對照後,這群漢人墾佃以及竹塹社頭人已自動視自己為土地的所有人了。從竹塹社七房眾人移轉到通土,通土同意漢人江顯為等拓墾;江顯為漢人進一步招來粵籍農民拓墾建庄;最後粵庄又把自己未墾的土地轉賣給陳長順,作為隘防之用。儘管巧立大租、小租、隘糧、現佃等極為複雜的土地所有權制度以狡飾其買賣行為,但究其實每一次的買賣,賣家都出賣了一些其實不屬於自己的權利,而不以農耕為基本生活型式的泰雅與賽夏則被排除在外。是可忍,孰不可忍?
告別下橫坑
道光元(1821)年也住在下橫坑的范長賡哭訴田園被風雨所毀,在債主逼迫下,闇然暫離下橫坑(何明勳 2015:10-15):
乾隆丁丑大風雨,[8]山崩地裂得人驚,田無蹤來畑無影,房屋倒下剩一半…黃某越來越無情,迫我賣山賣田畑,九百文錢可抵債,再增加添兩銀錢…田園已荒五六載,多荒幾年高不將,青山綠水永久在…不如暫離下橫坑。
也是這一年,失去長子已三年的羅鵬申舉家告別下橫坑,北遷八九公里外,鳳山溪對岸的汶水坑(今新埔鎮清水里);又十年後(1831)次子華招(1788-1831)也病逝,鵬申自己則以八十高齡於1837年壽終正寢;又十年後(1847),三子華五(1796-1877)帶著弟妹子孫遷居湖口糞箕窩。十九世紀的前二十年,整個飛鳳山丘陵是漢人與平埔侵墾,而泰雅賽夏反撲的世代;我的祖先羅華酉則只是這其中悲傷的片段罷了。
只是儘管悲酸無盡,飛鳳山丘陵這橫躺在頭前鳳山兩溪之間的等腰三魚形,終究還是成了漢人的囊中物;「蕃人」退去,它那南北向九公里長的底邊則成了漢人的通道,也就是臺三線的一小段。如果它浪漫,恐怕是因為我們對於歷史太多的遺忘與重建。
參考書目
何明勳口述,2015,《渡台記校注-燈前月下聽夜話》。臺北:五南。
吳學明,1998,《頭前溪中上游開墾史暨史料彙編》。新竹縣:竹縣文化。
張炎憲、王世慶、李季樺主編,1993,《台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上)。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室。
羅華五、羅景輝,1966[1859],《羅氏族譜》(不著書名)。新竹湖口:未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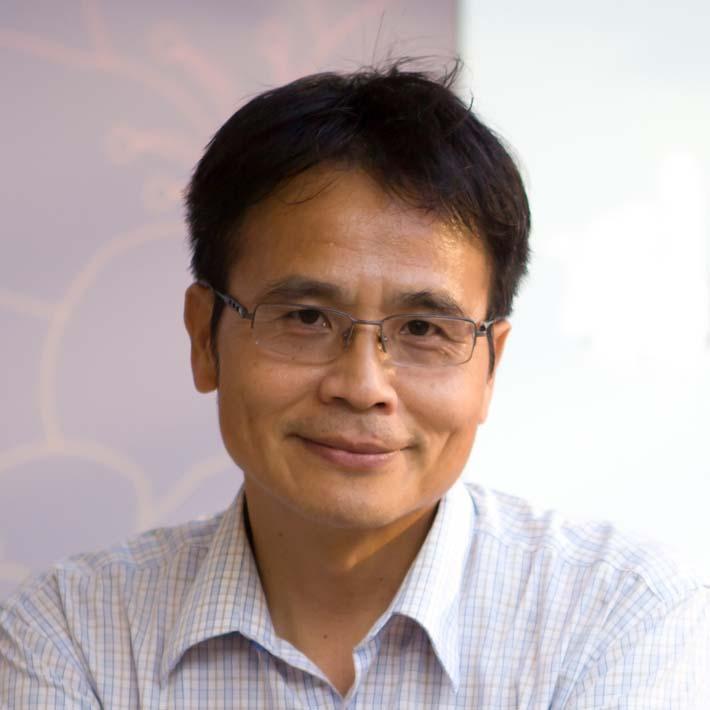

0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