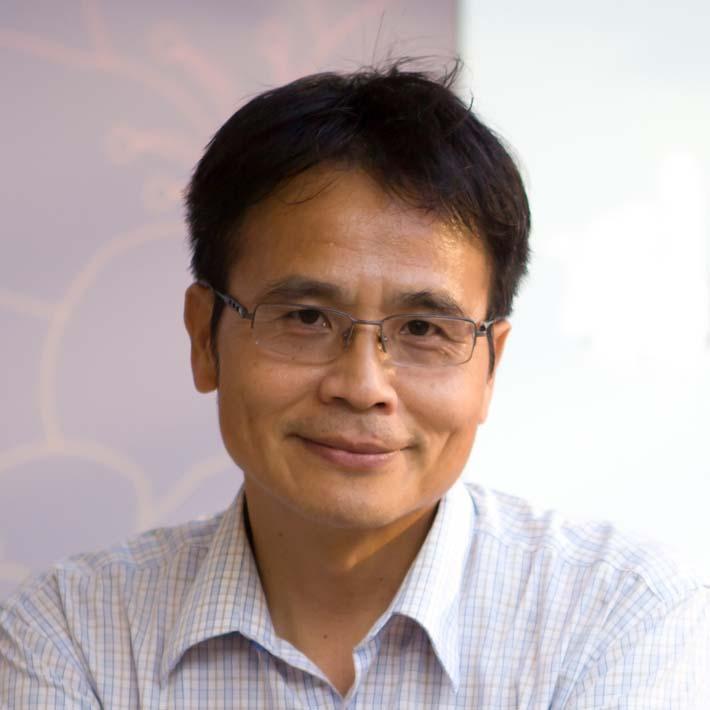•2015年3月28日 星期六,上午11:10
柑橘:山丘上的黃金
柑橘是臺灣秋冬當令的水果,果實酸甜多汁,剝皮方便,廣受歡迎。然而,我們此刻喜好的水果,倒不是往昔素有之滋味;而且,柑橘對於客家生計與命脈影響頗大,值得推敲。
種出蠻方味作酸
熟來包燦小金丸
假如移向中原去
壓雪庭前亦可看
這是臺灣文獻初祖沈光文(1613-1688)詠柑之作,顯然沈老嫌此果太酸,但賞其金黃色澤,所以才想移植北方,庭前賞雪,可堪為伴。這樣的番柑滋味如何呢?沈老的〈雜記〉有言:「有番柑,種自荷蘭,大於番橘,肉酸、皮苦。荷蘭人夏月飲水,必取此和鹽搗作酸漿入之。多樹園中,樹與橘無異」。正因為肉酸皮苦,較適合調製為飲料。
直到日本時代,柑橘才成為新興產業。相對於稻米與衣物等糧食或生活必須品而言,柑橘除非成為販售於市場的商品,否則其發展前景有限。然而柑橘卻易於腐敗,想要成為商品必須要解決運輸與儲存的問題。日本時代交通事業的發展與技術之開發,才真正完成了柑橘的商品化。在農業技術的進展方面,主要為栽培管理技術的進步以及栽培品種的改良。在銷售層面上,除了奠基於交通運輸網絡外,更由官民合作組成銷售組織。
日本時代,香蕉、鳯梨與柑橘成為臺灣三大水果產業,這類園藝產業在全臺產值中,僅次於米糖,居於第二位,也成為主要的農產品與貿易商品。
那麼,對於客家而言,柑橘產業的意義為何呢?關鍵於在柑橘適合生長於淺山地區,而這正是客家分布最密集的地方。從糧食生產的角度思考,平原地區的生產力較高,養活較多的人群;然而,山林卻能生產經濟作物,例如樟腦、茶及水果等,而經濟作物的價格又往往高於糧食作物。於是,淺山地區反而成為財富的來源。
東來竹郡扼雄關
好水縈洄又好山
到處人家柑萬樹
桃花不數武陵灣
正是途中見到客庄淺山上,處處柑橘的盛況。這些山林產業所創造的財富,使得臺灣內陸城鎮蓬勃發展,也是客家文化擴張的力量泉源。
有趣的是,這一產業也創造了桔醬這一重要的臺灣客家美食佐料。以酸桔製成的桔醬是北台灣客家庄偏好的蘸醬,用來搵食三層肉或水煮青菜,往往被視為客家菜的標準配備。然而桔醬其實卻是很年輕的食品,晚至日本時代才大量引入,遍植島內。由於桃竹苗地區淺丘地區是柑橘主要產地,自然也種植了可觀的酸桔樹,本地的客家人將酸桔去皮煮爛後,再用石磨磨碎,製成桔醬,從而成為餐桌必備。
而今,秋冬之際,城市之人頗愛進入客庄山林採橘,既親近大自然,也縮減了果農受產銷體系之控制,那山丘上的粒粒金黃,更是格外可口。
---------
註:原文發表於《客響電子報》,第29期,103/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