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7日 星期六,上午10:24
三、拉者的木屋
1840年,瑟冷布憑藉其近500公尺海拔的身形,睥睨腳下10公尺河岸平原上的這場王朝第一聖戰,很難不受注目。兩年後,布魯克重回被馬來人所放棄的新堯灣,訪視華人重建了的新聚落,並且登上了瑟冷布。這拉者顧盼自雄地讚道:「從本寧堯(Panonjow)起值得步行賞玩,沿路遠眺山丘、河谷與海洋,這真是絕妙的鄉野景觀。卓立於周遭石灰石崗阜之中,瑟冷布是如此壯麗!」[1]
布魯克筆下的本寧堯是當時瑟冷布山上三個比達友聚落之一,另外兩個分別為瑟冷布(Sarambo)與秉波(Bimbok)。於是布魯克在略高於三個村落的平曠之處,買下一些果樹作為補償金,使部份部落家屋往下遷移,並在比達友人的協助下,起造了避暑、度假與養病的木屋。[2]
從後來的紀錄看來,布魯克這山上小屋倒是往來無白丁,[3]其中又以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 1823-1913)最為知名。華萊士是英國探險家,或許他的名氣不如達爾文響亮,但是他在1855年寫作的《砂勞越法則》文章,卻促使達爾文寫下聞名世界的《物種起源》。也因此,學界其實已經把華萊士跟達爾文相提並論,認為是天擇說的共同發起人。華萊士1854年時,在拉者的木屋裡住了一陣子,並且在這附近收集了大量的蝴蝶和甲蟲類標本。值得注意的是,華萊士不僅收集生物標本,從他寫回倫敦的信中,我們看到他娓娓道來上山的路徑、聚落樣貌與家屋的形式、獵首舊俗、服飾、山居、體型以及飲食等。[4]拜拉者木屋訪客之賜,我們今天仍可以看到眾多瑟冷布三個比達村落的風土人情。
第二任拉者(1868-1917)繼任後,獵頭舊俗早已遠去,海達亞(伊班)與陸達亞(比達友)之間的緊張關係解決,砂拉越更加捲入世界體係,政治經濟局勢丕變,瑟冷布山上的比達友人開始向下向外擴遷。
本寧堯自瑟冷布向東向北遷徙,首先是本村Peninjau
Lama於1910遷至今址;又於1956年,新擴至Peninjau
Baru。另外,1942年Tibatu建村,至於Semaba及Sudud二者則不詳。
Bombok遷村更早,Sungai Pinang早在1888便下山,跨過砂拉越河,在北方新建村落;Kandis Lama也於1925建村,又於1963年,擴村遷徙到Kandis Baru。
最大的村落Serembau則向東、南、西三個方向遷徙,其村民與遷徙年代分別為Sega (1950)、Kopit (1960)、Segubang (1930s)、Sogo (1910)、Skio (1930)、Seromah (1900)、Seropak (1930)、Skiat Lama (1917)、Skiat Baru (1971)、Merembeh (1968)、Podam (1886)、Sibulung (1952)。[5]
我們現在其實還不確定瑟冷布三村大舉下山擴遷的原因,一如今日我們如果登上瑟冷布也完全無法理解為何他們要在這麼陡峭的山上生活。不過,我想應該與前述政治經濟捲入世界體系有關,廣大的砂拉越領土與資源召喚著更多的人群走入叢林。
這一點華萊士的態度即十分明顯,關心物種的華萊士顯然更關心人種的問題,他對新堯灣的觀察是:
山下有一個中國小販商的聚落,這村落遠比新加坡與麻六甲令人愉悅,因為成群的婦幼,使得聚落顯然自然而富家庭氣息。村內的女人大部份都是達亞人與中國人的混血,這提昇了他們(達亞人)的種族(體質),有些女人十分漂亮,除了很年輕的女孩外,完全看不出達亞血統。除了種族體質之外,當然在品德與政治上也有提昇。
儘管華萊士這一觀察充滿種族偏見,但是對於一個關心物種的學者,以這樣的觀點看待異族之人,並不特別讓人意外。他相信中國人的移入對砂拉越的整體人口,是很有價值的:
這些中國人是整體人口一個穩定而有價值的助力,在目前政治修明的情況下,本地出生的中國人漸增,而他們也逐漸與達亞人的混血,所以砂拉越的持續繁榮是指日可期的,而且這也將進一步影響廣大的婆羅洲。
書信的最後闡述讓中國人落地生根的主張:
有妻、有眷、有家、有國的男人才容易治理,因為他們比新加坡那些窮光棍要快樂滿足多了。這兒的中國人覺得他們是國家的一份子;他們不能只是被一群陌生人統治而已,他們的情感與偏見必須受到諮詢與尊敬,他們(對國家)長遠的利益在於他們不添麻煩,比任何其他東方世界,更易於服膺權威統治。
這雖然是華萊士的個人意見,但再參照前述聖約翰在初見新堯灣時所表露的情感,在在顯示十九世紀中期時,英國人對於引入華人至砂拉越的樂觀與積極態度。
從砂拉越後來的歷史發展看來,這樣的態度雖然因1857礦工事件頓挫,但是長期看來沒有太大的改變。比達友瑟冷布三村落自1880年代起,從瑟冷布往下往外播遷之時,也正是華人中斷近三十年後,重返新堯灣,再創繁華之日。吾人今日所見之新堯灣,其歷史可以追溯至此時。儘管文獻資料不豐,但新堯灣水月宮的匾額是最清楚不過的印記。我們就順著華萊士的思路,走下瑟冷布山,向北到那老巴剎一探華人的廟宇。
[1] Mundy, Rodney (1848) Narrative of Events in Borneo and the Celebes.
V. I, p.336。轉引自Martin Laverty (2011) ‘Serembu
settlements from 1839’,文件分享資料庫(http://www.slashdocs.com/),2013/9/29登入。以下多處轉引本文,不再詳述。
[3] 參考Martin Laverty所輯成,’S Spreading Down and Out: Serembu Settlements from 1839’,未刊稿,可參見http://archive.org/details/cu319240784096812。
[4] 本段及下段相關敘述皆引自華萊士於1854年所寫的書信,信件刊於Literary Gazette (London) 1855年6月9日版,頁366。依編者Charles
H. Smith的註解,這封軼名信件確係華萊士所寫,電子版可聯結:http://people.wku.edu/charles.smith/wallace/S018.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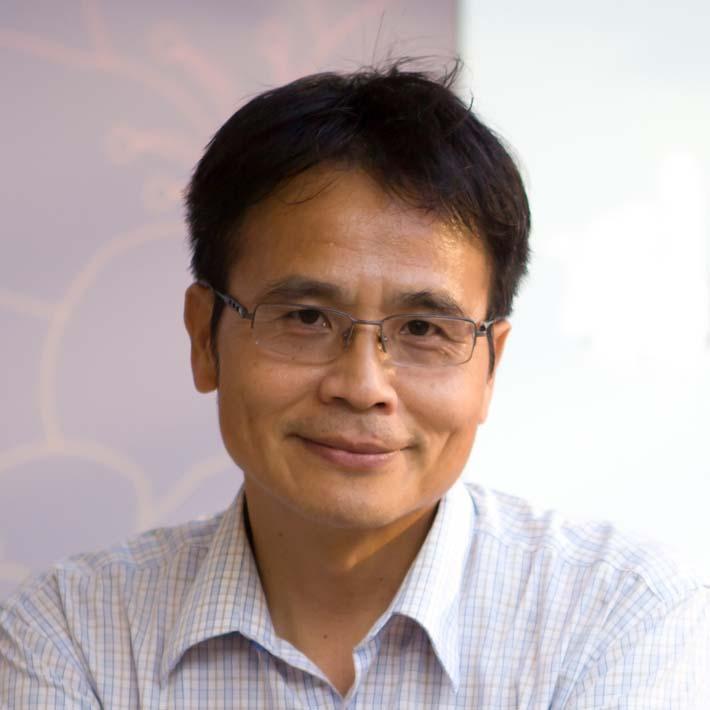

0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