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4日 星期日,上午10:41
竟然想哭!
「羅老師,你這顆牙裂開了,沒辦法,只能拔掉了!」牙醫拿了小鏡子,讓我自己也瞧瞧那裂縫;儘管她的語氣有禮而溫柔,但是一點也改變不了那殘酷的事實。
故事要先從古晉說起,那是抵達的第二天晚餐,我進了華人街區的福州餐廳,一盤深色的炒麵藏了硬骨,我一口咀嚼,左上顎一時痛徹心扉;然而,等待我的是十餘日的田調以及駕車幾百公里的旅程!
接下來的日子其實十分喜悅,華人街市、伊班與比達友村落太多有趣的事情;而我也很快學會與痛楚共存及對話。每餐飯謹慎地送到右側口腔,緩緩地咀嚼,反而感受了食物的滋味;刷牙也認真了,像個小學生般,認真地照老師的方法對待口腔。而且對於那顆痛楚,我小心翼翼地忍著隱隱的痛,硬著心腸,輕輕地刷洗它。
是田野生活的腎上腺素救了我嗎?還是我真的蒙古大夫地治好了它?我一無所悉。兩週過去,飛回臺灣,立刻插隊看了牙醫。原來是牙周的問題,我做錯事般,對於醫生的叮嚀猛點頭,表示一定改進,還會乖乖回來完成牙周療程。
為什麼想哭呢?故事似乎還更遙遠。
學院從新竹校本部搬來竹北饒平林姓聚遺址後,大學與社區的關係越來越緊密。起初,我只是想沿著灌溉水圳尋看,了解這高速鐵路設站,地景與居民丕變之後,那原初的田園,變成何種風貌。
走路不濟事,我開始跑步;而跑步,當然也因為兩年多疏於運動,體態懶腫。某個初秋雨毛的早晨,我才越過都市外環道路,田圃風圍瞬間奔赴目前。於是就著風涼,沿圳東行,發覺這樣的跑步似乎可以永不停足。
就這樣,我的跑程越拉越長,而我的體重則愈來愈輕。參加了半程馬拉松之後,又瞅著全馬報名單自我惕厲。腰帶環很快地回到正常的扣位後,居然又重返「輕」春往事;雙腿餘油則燃燒殆盡,令人撫捏自豪。於是耳中不乏「老師,怎麼您這多麼多年了,都沒有變!」「您身材是怎麼保養的啊?」之類的讚美,這些外交辭令可別當真,但入耳暈暈,還是教人暗自心爽。
偏偏跑步帶來的皮囊阿腴,穿著哲學外衣,讓知識份子昏了再昏。為了備戰全馬,我訂定了自我訓練課程,無論是速度跑或長跑,目標總是超越自己的現況能力。於是每次跑步都變成了多重自我對話的場域與時機,只要一到臨界點,顛躓的心肺與痠軟的肌肉便開始爭吵,但意志從來就否定肉體的主宰權,執意前行。就在一次又一次的肉體與意志的拉扯後,驀然發現好像有幾縷深邃的凝視,發自模糊的遠方未來,那是想當仲裁者的靈魂嗎?
我沒有解答,不過它讓人愉悅,因為接下來的日子,臨界點不斷地被推向更外更後的世界。肉體與意志仍復爭吵,但都愈發堅強。特別是苦練過了子夜之後,我藉瑜珈伸展,將身體攤開舒放在跑道盡頭時,那無垠的和諧世界,讓人愈陷愈深。
處理了大大小小的公私雜事,不過幾天,再度飛返古晉新堯灣田調,依舊享受了山山水水裡的奔跑。只是啊,不知知命之將至的我,在駕馭肉體而得意之餘,那痛楚就是沒有真的完全消失,它如細絲纏束,夜半格外有力。
再度回臺,依約進了診所。驚覺牙之痛楚不只是痛楚,而是它已崩壞。對於肉體崩壞又能如何?於是想哭,因為嗔戀身體。
------繼續閱讀:馬拉松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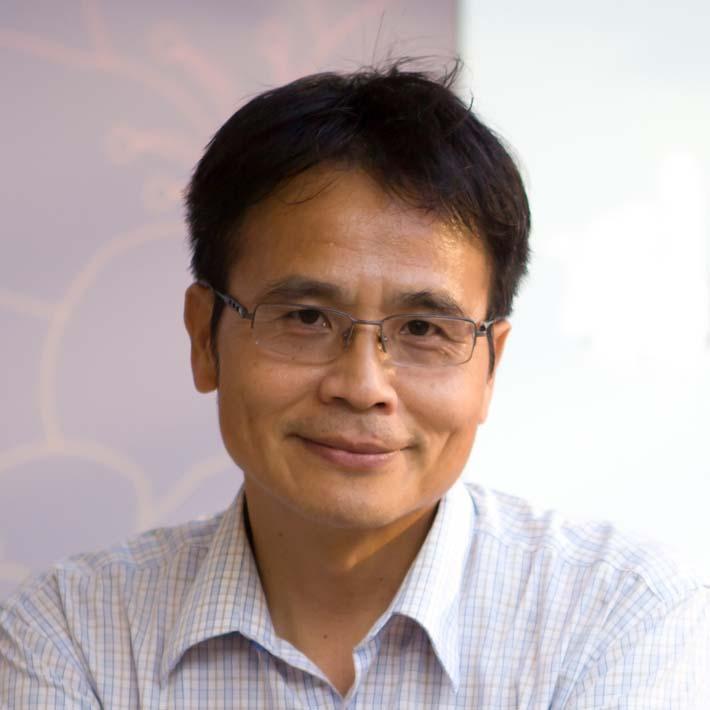

0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