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論文
台灣枋寮義民廟階序體系的形成
羅烈師*
摘要
枋寮義民信仰創造了一個包含神位、祿位與調位的階序體系,這一體系以義民神位為核心,將捐施與經理廟產有功者的祿位與祭典區內所有信徒的調位收納為一。體系的原動力是竹塹城外居民無主的恐慌,而決定階序高低的因素是廟產的捐施與管理。無主的恐慌包含兩種形式,其一為對別人無主而生的恐慌,一為對自己無主所致之恐慌,而這兩種恐慌在義民廟信仰裡,同時匯注於那場最初的恐慌,亦即對於林爽文役殉難者的恐慌。排解無主恐慌的辦法唯有使亡者有主,亦即將抽象的亡魂具象化為神主牌,有了神主牌之後,才能夠接受祭儀,安享蒸禋。為了安奉這方神主牌,勢必捐施土地產業以營造一處神聖空間;其次再分割神聖空間為高下階序,讓捐施者的祿位牌也得以安置。於是殉難者不再無主,捐施者也因此而有主。猶有進者,神聖空間的形式不僅包含廟宇內的神位與祿位,祭典組織裡的調單也逐漸被視為一種神聖空間形式。紅色醒目、大量印刷的調單被張貼在廟宇及家戶的牆壁上,紙上所有捐施者的名銜(調位)也彷彿成了具體而微的祿位。因此,藉由神聖空間的創造及分割,同時賦予階序,讓眾人透過捐施而有主,此即枋寮義民信仰之奧秘。
闗鍵字:義民、階序、調單、神位、祿位
The forming of the hierarchy of Yiming
Summary
The Yiming cult of Fangliao in
Key word:Yiming, hierarchy, donating
list, god tablet, emolument tablet
一、前言
本文所謂台灣枋寮義民廟階序體系係指廟內供奉的牌位以及祭典組織分工的調單上所顯示的高下排列關係,這一體系之形成以無主的恐慌為原動力,其階序關係決定於財產的捐施與經理,然而具有封神權力的帝國卻帶著族群異音,被安奉在頂端。
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於大里杙(今台中縣大里市)起事,同年攻陷竹塹城,林先坤等人組義民軍捍衛鄉土。役畢,義軍以牛車遍拾忠骸,計獲二百餘具。原擬歸葬大窩口(今新竹縣湖口鄉),車過鳳山溪,牽牛停蹄,不受驅策。於是就地卜筶,得「雄牛睏地穴」吉地,乃葬。此即今之義民塚,曾蒙乾隆皇帝「褒忠」敕旨。後林先坤等人再議建廟,廟成於乾隆五十五年(1790)。同治元年(1862)彰化戴潮春起事,義軍再組。嗣後迎葬是役百餘忠骨於原義民塚旁,是為「附塚」。光緒二十一年(1895)廟毀於甲午割讓,經理徐景雲等號召捐資重建,新廟落成於光緒三十年(1904)(財團法人臺灣省新竹縣褒忠亭1988:16-19)。目前枋寮義民廟的祭典區也含十五大庄,每年由一大庄輪值經辦該年
二、無主
義民是「孤魂野鬼」或「無主亡魂」嗎?這是台灣義民信仰的重大爭議之一,曾經在客家族群內引起喧然大波。[1]這一「義民神格」的問題,對庶民真實生活而言,正是「有主」或「無主」的恐慌。
「主」字屬於六書中的象形,遠古的造字者依據燈台的形象,創造出這個文字。主字上端的「、」即表示燈之火焰,而「王」則為燈台的形象。[2]由於火焰所具有溝通陰陽的特質,使得後代的文字使用者就用主字稱呼象徵神靈或祖先的牌位。[3]而所謂無主意即亡者沒有神主牌,或者其名諱沒能記載於神主牌位上,所以也就無法在歲時祭儀時,饗用蒸禋。竹塹地區的客語對於死者這種無主的狀態,稱為「無人承受」(mo ngi shen shiu),即一般漢語習稱之孤魂野鬼。
亡者斷氣、撒手人寰之時,死者的家屬為亡者洗身理容,並更換壽衣,是為「小殮」;隨後將亡者安放於棺木內,稱為「大殮」;再經家奠禮與公奠禮後,靈柩方得下葬。下葬之前必須請來有地位的人士擔任點主官,主持「點主」儀式。這一儀式必須事前準備一個尚未完成的神主牌,所謂尚未完成係指這個神主牌位上的「主」字會被寫成「王」字,必須加題一點「、」字,才成為一塊真正的神主牌。點主儀式中,孝子反手背持神主牌跪在柩前,點主官口頌「天地開張,日吉時良,點王為主,世代永昌。」並且手執毛筆,沾上朱砂,在神主牌之「王」字上方加題一點,成為主字,是為「點主」。前文所謂「承受」意即喪禮中兒子行點主儀式,承受了父母親的神主牌,自此依歲時而祭祀。
墓葬之後,喪家在家堂中設置靈桌,早晚在靈桌前,供奉日常飲食及洗臉水,並焚香、燒冥紙,稱為「奉飯」;直到百日方能將神主牌火化,另設香火籃掛置牆上,而將靈壇移除,是為「除靈」,喪事至此結束。墓葬之後三至五年,擇吉開墓,將骨骸拾入金斗甕中,是為「撿骨」或「啟攢」;最後再納入宗族共同的祖塔,稱為「晉塔」,而亡者的香火籃方可火化,並將名諱寫上公廳之大牌,亦即共同的神主牌位上,是為「合火」。[4]
一般而言,無主恐慌的解決依恃於宗族。生前與死後的世界,一陽一陰各有秩序,在宗族的層級內,二者合而為一宗族秩序。而喪葬禮儀的意義在於溝通陰陽,將死者納入宗族秩序中,從而讓死者得到一個確定的地位,安享歲時祭祀。在喪葬儀式中,亡者軀體經入殮而安放於靈柩中,在喪家的住屋裡,顯得十分龐大;靈柩下葬後,喪家則擺設靈桌與神主,相對於靈柩,體積大幅減小;再經百日除靈後,神主火化,改設相當輕巧的香火袋,安置牆上的吊籃上;最後,既經啟攢,骨骸晉塔,香火袋內的香火便與祖先的香火合而為一。從碩大的靈柩到合而為一的香火,喪葬儀式將亡者歸納到一個終極安寧的秩序。
喪葬不僅是具象地將亡者骨骸轉化為香火,從抽象的層面,我們在儀式中也可以看到溝通陰陽、引導亡魂的舉措。以喪禮中的「送火」(song fo)儀式為例,一旦生人頓入死境,立刻陷入茫然不知所措的局面。介於斷氣與下葬的停柩期間,死者尚能在家戶之內得到照顧,可以如生人一般享受日常飯菜,又像亡者那般安享清香;然而下葬當天起,亡者頓失依恃,儘管生者已將各式日用品,包含房舍、舟車、僕從等,火化相贈,但是亡者卻必須自理飲食。於是當天起,平日升火做飯的婦女便須連續三天送火給亡者。據說早期送火係用火把,近來則多用一束柱香代替,比較講究的喪家還會將柱香下半截竹枝折去,表示致送給亡者的不是柱香,而是火把的代替品。第一天送火必須直至墓地,並且面告明日送火之時間及地點,請亡者屆時前往接火;次日送火無須到達墓地,而是喪家至墓地路上,比較接近墓地的地方;第三日送火又則較接近喪家。因此送火儀式除了致送火種使亡者得以炊煮外,也同時具備指引亡者魂魄返家路途的意思。
透過這樣儀式上細緻的安排,亡者融入了宗族秩序;反之,如果亡者未能經由這套儀式安排,便會成為孤魂野鬼。而且,這種儀式上的安排並非一蹴而幾的,因為即使亡者已經融入宗族秩序,子孫仍須在往後的的日子裡,依歲時而祭祀,否則祖先依舊無所依恃。本文稱這種孤魂野鬼的恐慌為無主的恐慌,而且這種恐慌是多重的,一方面指的是擔心自己或家人死後會成為孤魂野鬼,另一方面也擔心陰界的孤魂野鬼會威脅自己目前在陽間的生活。這一無主的恐慌對於竹塹地區的移民而言,是格外嚴重的,因為這些離鄉背景的移民,已經無法祭祀自己的祖先了。以嘉慶三年(1798)五月間與妻子彭氏及子女共同來台的羅鵬申為例,當時四十一歲的鵬申由廣東陸豐縣河田墟遷居渡台,在苗栗中港溪口登陸。鵬申來台之後,汲汲於尋找足以安身立命的田地,而當時許多來自陸豐的客家鄉親,正於頭前溪與鳳山溪上游開墾田地。於是鵬申一家即前往關西下橫坑,投入開墾工作。嘉慶二十三年(1818),鵬申長子華酉當年三十六歲,於下橫坑慘遭泰雅族殺害。三年後,即道光元年(1821),鵬申一家九口放棄拓墾工作,由下橫坑徙居新埔汶水坑,佃耕田地為生。至道光十一年(1831),鵬申來台已三十三年,亦已高齡七十四,次男卻於本年病逝。鵬申接連痛失愛子,又隔海驚聞祖田丁份被奪,其叔姪及各從兄弟亦未如鵬申所託付,代為祭掃鵬申父母之墳塋。鵬申激憤之餘,立刻修撰多封家書,託往陸豐故鄉,企求親戚協助祭掃。[5]
這絕對不只是一個十九世紀初期新埔佃農的悲涼,它更是當時竹塹全體移民共同的傷痛。當時一張<大溪墘及大崙、白沙墩、紅毛港、大湖口四庄聯合建醮序>文中,如此形容這群無人承受的孤魂:「或為西州大賈,執紼無親;或為南陽行商,穹碑未記;或沙場無定,依然夢入深閨;或青塚徒存,猶是心期月鏡。」[6]序文中所謂四庄大致包含目前新竹縣新豐、湖口兩鄉以及桃園縣新屋鄉、觀音鄉南半部與中壢市西北一角,亦即新竹縣新豐鄉紅毛港溪與桃園縣觀音鄉大堀溪之間,25公里長海岸縣向東十餘公里以內,約250平方公里的區域。序文裡四庄移民客死異鄉者,雖身為大賈死後卻沒有親屬為他執紼營葬;有些行商被草草掩埋,連墓碑都沒有;或者征戰異鄉的兵丁,他們的妻子甚至不知自己的丈夫已化枯骨;而那些無人祭掃的墳塜,它們的墓主或許仍期盼那些已成鏡花水月般的壯志能達成。當然,四庄建醮序中對於無主亡魂的敘述,未必精確地呈現當時社會實況;不過,尋思文意,我們依舊可以感受到那份來自於無主亡魂的悲涼。
三、託孤
前文所提及的無主恐慌,在台灣十九世紀末那場反政府動亂的後續處置事宜中,更是顯而易見。事件之後的十六年(1802),竹塹人回憶:
丙午年(1786)冬,元惡林爽文戕官陷城,程所主遇害,壽師爺接任,立策堵禦,我義民墓勇,幫官殺賊志切同仇。捐軀殉難者不少,血戰疆場,屍骸拋露到處,夜更深常聞鬼哭,各庄人民寤寐難安,蒙
制憲以粵民報效有功,上奏京都,聖主封以褒忠二字,時有王廷昌自備銀項,請出鄧五得為首,各處收骸,欲設塜。[7]
這段回憶讓我們可以想像這些拋露到處的屍骸,對於竹塹那些尚未立穩腳跟的移民造成多麼強烈的心理壓力,莫怪乎竹塹人夜深常聞鬼哭,寤寐難安!這種恐慌與悲涼當然需要藉由信仰與儀式才能安定,於是才有收骸、設塜之舉。乍看之下,我們對文中所謂「屍骸拋露到處,夜更深常聞鬼哭,各庄人民寤寐難安」之語,可能會認為這無非文學修辭罷了。然而,另外兩紙文件可以進一步告訴我們,那種無主的恐慌是如此真實,不是個別文人的文采而已。這兩紙文件的簽署人為戴元玖子孫與王尚武,也就是施地捐資使義民廟得以構築的兩位重要人物。
乾隆五十三年(1788),林爽文事件平息後,「因塹屬地方陣亡義友骨骸暴露兩載乏地安葬,惟有戴禮成、拔成、才成兄弟丈義,為人喜施情殷,先年憑價承買…枋寮庄舊社空地一所,允愿發心樂施公塜」,而交換條件則是「而義祠工竣進火安香之日,眾皆樂迎戴府甫元玖公祿位牌登立龕位福享千秋」。[8]顯然戴禮成兄弟捐施土地的動機,係為確定其留住於大陸之父親戴元玖的祿位牌,能夠登龕立位,福享千秋。[9]一旦父親祿位得立,自然無須再有無主的恐慌。雖然往後兄弟遷往新竹縣湖口鄉拓墾,並且成為湖口重要的宗族之一,而且目前元玖的牌位也安置於宗族公廳之中;然而十八世紀末的拓墾年代裡,禮成兄弟當然無法預知自己未來的發展,不如眼前先將父親安頓妥當,了卻人生一樁大事。對於渡台初期的移民而言,這樣的心情十分真實,即使是遁入空門的的和尚也難自外,義民廟祝王尚武正是另一個顯例。
法號智武的王禪師本名尚武,祖父及父親原居住於興直堡的新庄街(即今台北縣新莊市),後來移居竹塹枋寮庄,剃度為和尚,既無親屬,也無後裔。乾隆五十六年(1791)一生克勤克儉的王尚武時年五十八歲,已屆暮年,雖積蓄了「老本銀」七百八十大元,卻十分惶恐於日後「香祝無歸」。於是尚武乃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
託孤字
立託孤王尚武,當年祖、父住在新庄街,後移居竹塹枋寮庄,釋事為業,壹生克勤克儉仍長有老本銀七佰八拾大元,今年五十有八歲,已無後裔,亦無親屬。此長銀項為僉舉的寔之人代為料理,誠恐日後香祝無歸,爰是設席請得義民亭首事王廷昌、吳立貴、黃宗旺、林先坤四人前來商酌。因其建立義民廟亭僅成後落正廳,其前堂并橫屋尚未有成,武願將老本銀題初參佰八拾大元,以為建造廟宇助成前堂橫屋之資。若後廟宇告竣之日,即將左橫廊武安鎮祖父及自己香火神主。又向眾商議,廟內香祝現料理,自備工食在外,仍長老本銀四佰大元,仍請首事王廷昌、吳立貴、黃宗旺、林先坤等合眾商議,即將老本四佰大元當眾交出,公舉交帶林先坤親手收存,每年每元議貼利銀谷壹斗
朝隆五十六年二月初二日[11]
王尚武的積蓄十分可觀,當時可以讓竹塹九芎林地區招墾
義民廟建成之初,僅有後堂正殿,以四合院的標準而言,尚欠前堂及兩邊橫屋。由於尚武擁有「老本」七佰八十大元,於是便將其中三百八十大元捐出,作為與建前堂與橫屋之資,其餘四百大元則由林先坤代收,每年應支付實物利息稻谷四十八石,其中十石由尚武領回做為伙食,其餘則每年生放累積,以便將來購置田業。相較於前述戴元玖合議字僅將香火神主事宜安排在合約的協議事項內,本託孤字則直接以香火神主為契約主要內容,其餘事項則係為此而安排。尚武之所以捐出七百八十大元的主要原因正是擔心將來祖先及自己的香火牌位成為無主之「孤」,於是要求義民廟新建左邊橫屋作為安置尚武祖、父及自身神主牌位之所。
以上三份文件顯示,人死後的超自然裡,可以區分成有主與無主兩個世界,無主的恐慌在往後義民廟史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就廟史初期而言,它促成戴王義舉;就往後而發展而言,它使義民廟的中元祭典廣為各村落參與,從而成為竹塹地區的信仰中心。下文我們先繼續沿著設塜建廟的線索,考察義民廟初期歷史;至於中元祭典與廟史中期以後的發展則隨後再談。
四、褒忠
除了竹塹人對於無主亡魂的悲涼與恐慌促成王廷昌自備款項撿收骨骸、戴元玖施地、而王尚武捐資,建成了枋寮義民廟外,必須一提的是,設塜建廟的行動與皇帝的統治權威也息息相關。林爽文之亂後,乾隆皇帝對台灣各祖籍人群的獎恤是:
此次勦捕台灣逆匪,泉州、粵東各莊義民隨同官軍打仗殺賊,甚為出力,業經降旨賞給「褒忠」、「旌義」里名匾額。其漳州民人有幫同殺賊者,亦經賞給「思義村」名,以示勸勵矣。因思該處熟番協同官軍搜勦賊匪,俱屬急公奮勉。而生番等自逆首窮蹙逃竄之後,經福康安明白曉諭,各社生番咸知順逆,幫同官兵、義民分路堵截,賊匪林爽文、莊大田無處逃匿。現在二逆首俱已先後就擒,所有打仗出力之熟番等,著賞給「效順」匾額,交福康安仿照各村莊義民之例,於所居番社,一體頒賞,以示旌獎。[13]
由於林爽文為漳州人,反清旗幟豎起之同時,各地不同籍貫人群的緊張關係也同時被挑起。因此泉州及粵東之移民便為帝國所組織而參與「平亂」,事罷,泉籍及粵籍分別獲頒旌義與褒忠匾額,以為獎勵。然而漳州及生熟「番」亦有協同官軍作戰者,因此乾隆再各頒思義與效順匾額。這些頒給泉漳粵番四大祖籍人群的匾額無疑是帝國對台灣地方社會的籠絡懷柔,然而它們所受到的待遇卻不盡相同。
乾隆的本意是頒發匾額後,讓各祖籍人群依式摹刻,並且懸掛在村落出入口醒目處,作為坊牌。南台灣屏東地區褒忠坊牌的摹刻較為普遍,目前南台灣客家所謂六堆聚落中,至少左堆之佳冬鄉與新埤鄉都還存在「褒忠柵門」遺跡。這些柵門具有防禦功能,約築於林爽文事變後的嘉慶年間(1796-1819)。其中佳冬鄉佳冬村尚存東、西、北三柵門,其中西柵門保存較完整,此門以紅磚、白灰、和少許木材混合建成,屋頂有燕尾飾,門額有彩繪浮雕,中央寫有模拓乾隆御筆之「褒忠」兩字(卓克華 1996;郭維雄 2002)。除了褒忠高懸在南台灣村落的柵門外,其他三式匾額則似乎未見有這樣的現象。然而,這四式匾額在往後歷史中引人注意之處,不在坊牌而是它後來被賦予神聖意義。
如前引枋寮義民廟文獻所提及,竹塹城外林爽文事件的殉難者亡命於乾隆五十一年(1786),而後屍骸曝露兩年,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事變平息後,「蒙 制憲以粵民報效有功,上奏京都,聖主封以褒忠二字」,城外居民才有收屍營塜的計畫。我們已無法確定這一文獻是描述史實,還是歷史的記憶,不過我們可以這麼推論,如果這是史實,那麼皇帝的封賜直接促成營塜的義舉;如果是記憶,則正好顯示了城外居民對帝王恩賜的重視。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帝國的恩典對營建枋寮義民廟塜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台灣重要的地方信仰如媽祖、保生大帝、開漳聖王及三山國王等,都有一個合法化的論述過程,而帝國都在這論述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宋元明清四朝總共褒封媽祖三十餘次,封號也由二字累加至六十四字,爵位更從「夫人」、「天妃」、「天后」、而「天上聖母」,歷代帝王不僅對媽祖頻頻褒封,還由朝廷頒佈諭祭以及文人參與(李露露
1994;張珣 2003)。保生大帝,宋孝宗乾道七年賜號大道真人,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加封為慈濟醫靈妙道真君萬壽無極保生大帝(魏淑貞
1994)。開漳聖王陳元光歷代屢有封贈。唐開元四年(716)詔立廟,封「川侯」。五代時贈封「保定男」。宋代追贈「輔國將軍」、「靈著順應昭烈廣濟王」、「開漳主聖王」。明初封「昭烈侯」。至於三山國王的身份,根據乾隆九年(1744)台南三山國王廟古碑所引劉希孟〈三山明貺廟記〉,所謂三山指的是獨山、明山與巾山,隋代時有神三人出現於巾山,自稱受天所示,要掌管這三座山。到了唐代元和十四年(819),韓愈被貶潮洲,遇上久雨不停,危害農稼收成,韓愈向三山國王祈求果真靈驗。宋代宋太宗征討中原,因三山國王顯聖宋軍大勝,詔封巾山為「清化威德報國王」、明山為「助政明肅寧國王」及獨山「惠威弘應豐國王」(邱彥貴
1993;陳春聲;1996尹章義 1999)。
台灣地方民間所信仰主神的成神過程,其實在漢文化裡源遠流長,早在戰國時代的經典<禮記.祭法>裡,便已規定了祭祀對象的資格: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眾;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眾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14]
文中所謂「聖王之制祭祀」正是後代帝王封贈地方神靈的理論基礎,受封者自此成為可祀之神,而封贈者則成為聖王,這也就是Watson(1985)所謂「標準化」的觀點。標準化並非意圖限制信仰的發展,反而賦予地方信仰一個全國性的合法地位,從而愈發昌盛。
吾人細繹當日文獻,乾隆皇帝所頒實為里名匾額,亦即對居民村里的賞賜;然而,有趣的是,這些匾額卻被台灣的漢人用來褒揚殉難者。四塊匾額中,泉籍與粵籍的旌義與褒忠最為兩籍人士重視。北港鎮附近的泉州籍殉難者,被安葬於北港旌義亭,後改為義民廟,廟址即在聞名遐爾的雲林縣北港媽祖廟附近。廟後由北港街紳商總董樹立墓碑,上刻「大清皇恩寵賜旌義忠魂同歸」字樣。這座義民廟的祭祀圈北至虎尾惠來厝一帶,南抵鹽水港附近,可謂盛大。此外,高雄縣大樹鄉水寮村也有無水寮義民爺,每逢
帝王的魅力並未隨著十八世紀末枋寮義民廟之建成而結束,「此廟建成十餘載,各庄人等同心協力,立有義民祭祀甚多,惟廟內崇奉 聖旨及程所主未有祭祀」,[16]於是村落的領袖又捐款購地,作為祭祀聖旨與殉難的淡水同知程峻的香燈業地。[17]也就是說,城外居民不僅安葬並祭祀殉難義民,甚至帝王頒贈「褒忠」匾額的聖旨以及竹塹城陷當天殉難的淡水同知程峻,都在居民崇祀之列。
顯然乾隆並未封贈義民為神,他只是以四塊匾額嘉許各籍人民之忠義,然而台灣漢人卻自行將這種殊榮轉移到殉難者身上。即使這種恩寵可以轉移到殉難者身上,也僅只於褒揚其忠義精神,而非封贈義民予王侯之品秩。僅管如此,不具神格的義民,卻仍然被台灣漢人透過神聖的儀式崇拜,而逐漸被神化。
五、牌位
十八世紀末竹塹城外的殉難者在戴、王施地捐資及帝國賜匾褒揚下,成為有主義民,其骸骨合葬義民塚內,其牌位則安奉於義民廟裡。戴氏兄弟所捐土地創造了一個神聖空間,一方面安奉殉難義民之牌位,一方面也使自己的牌位陪祀於正殿;王尚武的捐獻則擴大了原來的神聖空間,也替自己的牌位找到一個永恆的歸宿。戴王兩人的行動成了往後義民廟史的典範,眾多對廟產有功的人也如戴王兩人一般,其名諱刻於祿位牌上,安享蒸禋。
目前我們在枋寮義民廟內可以看到十三塊牌位,供奉著二十個神位及祿位。廟內為什麼會供奉這麼多牌位呢?這些牌位又是在何種歷史過程中,被安奉在廟內?以下我們透過牌位的分類分析,回答這些問題。十三個牌位可依空間分布可以區分為三個區域,分別為正身(zhengshen)與兩邊的橫屋(vangvuk)。正身中間供奉「敕封粵東褒忠義民之位」,左側分別為「觀音佛祖」、「神農皇帝」、「三山國王」,右側為福德正神與戴、王兩施主;左橫屋有林、劉施主及大先生陳資雲三方祿位牌;至於右橫屋則有三方祿位牌,但是供奉十個祿位(參考表1及圖1)。
表1 台灣枋寮義民廟供奉牌位一覽表
|
編號 |
牌位 |
位置 |
人物 |
備註 |
|
正 身 |
||||
|
1 |
敕封粵東褒忠義民位 |
明間 |
義民 |
林爽文與戴潮春兩役之殉難者 |
|
2 |
觀音佛祖神位 |
左次間中位 |
|
|
|
3 |
神農皇帝神位 |
左次間左位 |
|
|
|
4 |
三山國王神位 |
左次間右位 |
|
|
|
5 |
福德正神神位 |
右次間中位 |
|
|
|
6 |
開山襌師祿位 |
右次間左位 |
王尚武 |
捐資興建廟屋 |
|
7 |
施主祿位 |
右次間右位 |
戴元玖 |
捐墓地與廟地 |
|
龍邊橫屋 |
||||
|
8 |
創建施主祿位 |
中位 |
林先坤 |
創建四姓首事之一、捐施田地 |
|
9 |
大先生祿位 |
左位 |
陳資雲 |
大先生 |
|
10 |
施主祿位 |
右位 |
劉朝珍 |
捐施田地 |
|
虎邊橫屋 |
||||
|
11 |
施主兼原經理祿位 |
中位中央 |
蔡景熙 |
誥封奉政大夫欽加同知御賞戴藍翎 |
|
施主兼原經理祿位 |
中位左邊 |
潘澄漢 |
欽加五品御候選分州賞戴藍翎 |
|
|
施主兼原經理祿位 |
中位右邊 |
詹崇珍 |
例授登仕郎翰林院待詔諡創裕 |
|
|
12 |
創建施主之祿位 |
左位中央 |
王廷昌 |
創建四姓首事之一 |
|
創建施主之祿位 |
左位中央 |
黃宗旺 |
創建四姓首事之一 |
|
|
創建施主之祿位 |
左位左邊 |
吳立貴 |
創建四姓首事之一 |
|
|
創建施主之祿位 |
左位右邊 |
錢茂祖 |
捐水租 |
|
|
13 |
重脩廟經理祿位 |
右位中央 |
傅萬福 |
重修廟宇之經理 |
|
重脩廟經理祿位 |
右位左邊 |
徐景雲 |
重修廟宇之經理 |
|
|
重脩廟經理祿位 |
右位右邊 |
張裕光 |
重修廟宇之經理 |
|
資料來源:抄錄自枋寮義民廟內牌位。
這些牌位包含兩種超自然界存在,一為神,一為超自然人,神有神格,享有神位;超自然人對廟產有貢獻,則有祿位。擁有祿位的超自然人又可分為兩種,一為捐施廟產者,一為經理廟產者。由於漢人的方位本身即有高下差別,其法則為「中最尊、左為次,右為末」。依此,則廟內牌位顯示出一個階序關係:神位高於祿位;捐施廟產者之祿位高於經理廟產者之祿位。
義民廟正身之牌位以神為主,這些神位包含義民、觀音、神農皇帝、三山國王及福德正神。義民是主神自然設於正中,觀音等神安奉於正身左側,並不表示其神格低於義民,這是賓主之分,無關位階高低。福德位於正身左側是漢人寺廟之通例,代表廟地本身之土地神。正身的特例戴王兩位施地捐資的地主,雖然不具神格,但其祿位牌卻安置於正身左側。大致上我們可以主張正身所供奉皆為神位,至於兩位施主之祿位則屬例外,後文連同其他例外一併解釋。
|
戴元玖 |
福德正神 |
王尚武 |
粵東褒忠義民位 |
三山國王 |
觀音佛祖 |
神農皇帝 |
||
|
|
||||||||
|
王廷昌 |
天井 |
劉 朝 珍 |
||||||
|
黃宗旺 |
||||||||
|
吳立貴 |
||||||||
|
錢茂祖 |
林 先 坤 |
|||||||
|
詹崇珍 |
||||||||
|
蔡景熙 |
||||||||
|
潘澄漢 |
||||||||
|
張裕光 |
陳 資 雲 |
|||||||
|
傅萬福 |
||||||||
|
徐景雲 |
||||||||
|
圖1
枋寮義民廟牌位位置圖 |
||||||||
龍邊橫屋三方祿位牌分別供奉林、劉二位創建施主及
虎邊橫屋也有三方祿位牌,但是卻稍嫌擁擠地供奉十個祿位。三方牌位分別為原經理、創建施主與重脩經理。蔡景熙、潘澄漢及詹崇珍是光緒八年至二十年(1882- 1894)的經理,因此被稱為原經理,供奉於中路;傅萬福、徐景雲及張裕光則是甲午割讓廟燬於戰火後,重建義民廟的經理,供奉於左路。至於右路一方牌位,供有創建施主王廷昌、黃宗旺、吳立貴及錢茂祖四人之祿位,則為廟史初期的廟產捐贈者(參考表2)。這一位階本應供奉於較為尊貴的龍邊橫屋,但卻被冷落到虎邊,亦屬例外,容後再敘。換言之,我們亦可以主張:對廟產經理有功者可以在虎邊享有祿位牌。
表2 義民廟清嘉慶年間捐獻名冊
|
項次 |
時間 |
捐施者 |
捐施項目 |
備註 |
|
1 |
1801 |
四姓首事 |
田二處 |
王廷昌、黃宗旺、吳立貴、林先坤 |
|
2 |
1802 |
四姓首事 |
水田一處 |
王廷昌、黃宗旺、吳立貴、林先坤 |
|
3 |
1814 |
林次聖 |
水租二石三斗 |
六家林家之嘗會 |
|
4 |
林浩流 |
水租三石五斗 |
六家林家之嘗會 |
|
|
5 |
林仁安 |
水租九石二斗 |
六家林家之嘗會 |
|
|
6 |
錢子白 |
水租三石五斗 |
竹塹社人 |
|
|
7 |
錢茂安、茂聯 |
水租二石 |
竹塹社人 |
|
|
8 |
錢甫崙 |
水租三石五斗 |
竹塹社人 |
|
|
9 |
1817 |
劉朝珍 |
小租谷三十石 |
|
資料來源:依《粵東義祀典簿》等義民廟古文書整理。
綜合前述義民廟二十個牌位的分析,由於神位、施主祿位、經理祿位等三類牌位正好分別位於正身、龍邊、虎邊,由於方位本身具有階序性,因此我們可以主張義民廟存在一個牌位階序,而這個牌位階序告訴我們:神位高於祿位,捐施廟產勝過經理廟產。前文已言及,神位係因受封於帝王,故可高坐正身;祿位依附於神位而存在,而其附麗於神位的資格則來自於對廟產有所貢獻。這意謂徒有神位不足以自存,神位必須安置於一特定神聖空間,祭祀神位之費用亦有賴於產業孳息,而這二者皆端賴廟產之建立。
那麼如何解釋那些例外呢?戴元玖與王尚武為什麼可以供奉在正身?創建施主計有林先坤、王廷昌、黃宗旺、吳立貴、錢茂祖等五人,但為什麼只有林先坤供奉在龍邊橫屋,其他都在虎邊?施主劉朝珍為何供奉在龍邊?陳資雲並未捐施廟產,又為什麼可以安奉在龍邊?
相對於其他台灣漢人廟宇,義民廟的祿位牌確實多得非比尋常。就一般廟宇而言,供奉主神及祀神外,另有土地神及地基施主。以這樣的慣例相比較,戴、王二人作為地基施主而供奉於正身,是合於一般習慣的。
龍邊僅有三塊牌位安奉三個祿位,相對於虎邊的擁擠,可見林、劉施主確實享有較高的階序。依同治四年(1865)的廟民廟記,四庄輪值經理義民廟產時,即已約定各項簿冊抄寫一式三份,兩份由林、劉施主保管,一份經理人遞交。[18]這顯示林、劉已經被視為是廟產的捐贈者,故稱「施主」。二十世紀成立管理委員會時,林、劉施主也各享有一個當然管理委員的名份。林劉既然是廟產施主,將祿位安奉於龍邊自無疑義。
至於王廷昌等所謂四姓首事(詳見下文)屈居虎邊,則較費思量。目前為止,我們所知有限,僅能確定在廟史早期具有重要地位的王廷昌等人,在十九世紀中期後已經不具重要地位,在往後的廟史中地位被林劉取代,於是日本明治三十二年(1904)年重建廟宇安排祿位時,就被排到虎邊。我們前述捐施廟產則安奉龍邊的原則,顯然不敵個別行動者的權力捭闔。但是這也並不表示階序原則可以完全被掙脫,據說日本明治三十二年(1904)義民廟重建竣工後,當義民及諸牌位轉火之時,林家曾有將戴元玖牌位轉置橫屋之議,而引發喧然大波。[19]戴元玖之子孫除於十八世紀末捐施廟地之外,相對於十九世紀初期的四姓首事,以及中晚期的林、劉施主,對義民廟的發展貢獻無多。儘管如此,戴氏宗族以八人大轎扛著族長
六、經理
前段所言之牌位階序,並非一蹴而幾,實際上它的形成過程持續了整個十九世紀。枋寮義民廟雖經戴元玖與王尚武施地捐資,但是「憑依雖有,嘗祀尚無」,亦即雖有廟塜,但是卻欠缺祀典費用。[21]於是「嘉慶六年間林先坤倡施水田於前座落新社墘東南角水田弍段,至十九年則林次聖施水租二石三,林浩流施水租三石五,林仁安施水租石二,錢子白施水租三石錢茂安、聯共施水租二石,錢甫崙三石,亦共施水租以成美事。至嘉慶二十二年(1817),劉朝珍繼施水田於後座落二十張犁南勢水田
表3 枋寮義民廟組織體系變革表
|
年代 |
廟產 |
祀典 |
|
1791-1816 |
首事:林先坤(林國寶) |
四姓爐主、首事 外庄中元爐主、義民嘗會 |
|
1817-1834 |
首事:范長貴、林國寶、姜秀鑾 |
林劉施主、外庄中元爐主 |
|
1835-1846 |
外庄經理 |
十三庄爐主 |
|
1847-1913 |
四大庄輪值經理 |
十三(四)庄爐主 |
|
1914-2004 |
協議會、管理委員會 |
十四(五)庄爐主 |
資料來源:整理自義民廟古文書。
枋寮義民廟的雙元體制係長期演變的結果,這期間最關鍵的文書是四姓首事簽署於嘉慶七年(1802)的<同立合議規條簿約字>(以下簡稱四姓規約),全文抄錄如下:
同立合議規條簿約字人褒忠亭首事王廷昌、黃宗旺、林先坤、吳立貴等,丙午年冬,元惡林爽文戕官陷城,城所主遇害,壽師爺接任,立策堵禦,我義民墓勇,幫官殺賊切同仇。捐軀殉難者不少,血戰疆場,屍骸拋露到處,夜更深常聞鬼哭,各庄人民寤寐難安,蒙
制憲以粵民報效有功,上奏京都,聖主封以褒忠二字,時有王廷昌自備銀項,請出鄧五得為首,各處收骸,欲設塜廟。相有地基,立買成就。遂即設席請得義首林先坤、黃宗旺、吳立貴等,合眾商議。痛此義民死者,淒青靈於墨夜,暴白骨於黃沙,營埋忠骸於青塜,以免陰靈怨哭如他鄉。呈請制憲大人,蒙批准:該義首王廷昌、黃宗旺、吳立貴、林先坤偕同粵庄眾紳等立塜建廟。戊申冬平基,已酉年創造,至庚戌年冬,廟宇完峻。辛亥年
批明 林先坤親收料理生放建廟仍長銀二百大元,利銀加壹五;又親收料理廟祝王尚武託孤字銀四百大元,利谷參拾捌石,立批是寔為炤。
再批明
林先坤男係林國寶,四姓面對新社螺蟧庄收租谷五拾五石,立批再炤。
再批明
林國寶當眾面限明年母利並谷利,又另收去田租谷,至明年冬一概付出買業,如無概交,仍依照議定貼利,日後經眾會算取出,批炤。
再批明
後日聖典開祭,文武秀士准領豬肉壹斤,廩保准領豬肉一斤半,舉人准領貳斤,進士准領四斤,監生准領半斤,貢生准領壹斤,州同准領壹斤半,批炤。
再批明
首事王廷昌、黃宗旺、林先坤、吳立貴等當眾廟內簿四本、立約四紙,各姓執簿約壹紙,後日照簿約均行,不得反悔,亦不得己大言生端等情,批炤。
嘉慶柒年壬戌歲十月 日
立同議合約人(條)
王廷昌
林先坤
黃宗旺
吳立貴[23]
這紙四姓規約直接的約定內容是歷年廟產的處分事宜,然而筆者認為它更可以看成是枋寮義民廟歷史上的憲章,義民廟的「外庄經理廟產」與「中元祭典由外庄主調」兩大發展主軸,都發軔於此。下文首先分析外庄經理廟產,下節再及中元祭典外庄主調。
本約簽定時,林先坤經管兩筆款項,一項是廟成之後的餘款二百大元,另一是王尚武捐款的餘款四百大元。四姓首事協議不計十餘年來的利息與利谷,僅約定依原初利率將六百母金生放予林國寶,一年後歸還母利,尚有進者,除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這筆款項之外,嘉慶七年(1802)農曆十月四姓首事又各分別捐出十百一十元,以三百三十元及一百零五元向周龍章購得新社螺嘮庄土地兩筆,契約中亦申明「付與褒忠義亭首事永遠管業以為香燈祭田」。[24]依「四姓規約」,這兩筆田地可租谷五十五石,而且四姓捐資購買土地的原因係義民廟「…建成十餘載,各庄人等同心協力,立有義民祭祀甚多,惟廟內崇奉 聖旨及程所主未有祭祀」。文中所謂聖旨乾隆的「褒忠」二字,至於程所主即林爽文事件中殉難的淡水廳同知程峻。為了每年聖旨與程峻的「聖祭」不虞匱乏,四姓乃出資購置土地,以為香燈祭田。這筆五十五石的租谷也須要四姓首事公推一人管理,於是眾議又將租谷交代林先坤的三男林國寶料理。如此一來,林國寶等於同時管理義民廟的三筆財產,可謂義民廟產實質上的經理人。[25]
四姓規約的主要目的是處理懸宕十餘年的財務問題,而且同時也值得注意的是,這群熱心於義民廟務的地方菁英不僅注視眼前,更已著手規畫未來。他們顯然相信義民田業會逐漸殷盛,因此甚至已經約定一旦租谷達到二百石時,將每年抽出五元於中元時備辦桌席,敬奉四姓祖父;一旦超過二百五十石,更將開祭四姓首事之祿位。那麼,如何促使這一局面早日到來呢?四姓首事「僉舉外庄誠寔之人輪流料理」,亦即建立一套適切的經理人制度。
儘管嘉慶七年(1802)四姓規約提出了「外庄輪流料理」的經理人觀念,可是矛盾的是,四姓首事最後仍決議先由四姓之一林先坤之子林國寶擔任財務的實質經理工作。所謂的外庄經理遲至1838年由新埔金和號等商號接手時,才初步開展;又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開始實施四大庄輪值經理時,才算比較成熟。從乾隆五十五年至道光十四年(1790-1834)間可以稱為未制度化經理人時代,乾隆五十五年(1790)廟成之後,四姓負責祭典,四姓各有首事,且輪值擔任爐主。此時尚未有廟產,但有銀元六百大元,由四姓首事之一林先坤管理。此時雖因未置田產,故而未有經理之名,但是林先坤經管義民廟資產,實質上可以看成是義民廟的經理。嘉慶六年與七年(1801與1802)義民廟購得田產四方後,林國寶繼承父親經理的工作,而且嘉慶七年(1802)「經理人」這一名詞也正式出現。正如經理人的概念逐漸浮現,爐主首事也開始鬆動。鬆動的不是爐主首事制度本身,而是爐主首事資格開始改變。起先爐主首事僅限四姓,但是從目前可以掌握的資料看來,至少道光九年(1829),原四姓首事僅剩林姓之林國寶,另外增加了范長貴與姜秀鑾。[26]而且在這期間義民廟田產快速增加,除前述嘉慶六年與七年(1801與1802)四塊土地外,嘉慶十九年(1814)獲贈林家及錢家水租六處,計十九石;嘉慶二十二年(1817)則又有劉朝珍捐施位於東興庄二十張犁南勢田地六十石小租之一半,亦即三十石。
道光十五年(1835)議定祀典簿後,廟經營史進入外庄經理人時代,祀典簿中已經具體載明經理人的工作條款。雖然目前的資料無法證明1835年祀典簿簽訂之後,義民廟隨即設立了經理,但是至少林施主收執簿顯示,道光十八年(1838)的經理人是金和號與榮和號。其規約如下:
一議本祠蒸嘗原為祀典並脩墳廟之資,非此事不得濫用,即有當用之項亦必勿眾酌議;
一議蒸嘗既大必須公舉的實之人經管,非公舉人不得擅收;
一議經管收理之人壹年既滿,即交下眼首事經理,其交下眼時,流水簿及各單并簿尾銀數,一齊交明算清;
一議簿尾銀若多,倘有殷實生借向經管人支出,字約經理人收存;若簿尾銀少則經管人收存至次年交出,不得少算;
一議眾立總簿四本每年
一議每年現時經管收理之人至行禮後,眾頒豬胙四斤;
一議嘗內谷係經理人收存,每車眾處倉耗谷若干,倘有缺少係經理人賠補;
一議所有田園至賃滿轉批,現年經理人必須通眾佃戶須席請幾位老成到場,不得私相授受,其文約經理人收存;
一議十三庄內若有中式者到義祠掛匾花紅銀拾貳元;內地來者花紅銀肆元;在台中考者花紅銀捌元;至貢生等不能友花紅,永為定例,議是實;
一議所有新舊科秀才廩貢們前來義亭拈香者,給金花紅永為定例是實。
外庄經理人的時代顯然姜秀鑾是重要推手,「道光壬寅二十二年(1842)九芎林姜秀鑾等具帖請得新埔街榮和號、金和號、振利號、雲錦號、錦和號、慶和號等輪流經理,至公無私,甲辰修理祠墓之資而由裕也。」然而新埔街上的商號日久生煩,認為粵籍人士應當共同承擔這項經理工作,因此道光二十七年(1847)林茂堂等十六人重新議定章程,將所邀人士鬮分為四大庄,大湖口等庄拈第一鬮,石岡子等庄拈第二鬮,九芎林等庄拈第三鬮,新埔街等庄拈第四鬮,每庄分理三年,輪流交遞。[27]至此,嘉慶七年(1802)所提構想「四姓僉舉外庄誠寔之人輪流料理」才算落實。目前所見資料,從道光十八年至民國三年(1838-1914)間,四大庄輪值經理廟產的共識,大致已實現(參見表四)。
我們仔細分析外庄經理人制度的歷史,會發現四大庄經理的時代其實不太順遂,如表四所示,道光二十七年(1847)開始的四大庄經理第一輪完成後,按約定大湖口應於咸豐九年(1859)接任經理,然而大湖口拒絕了,於是新埔街連任九年,顯然另外兩庄也無接任。這個問題如何解決的呢?無巧不成書,同治元年(1862)中部地區發生戴潮春亂,竹塹城外亦組義軍隨官軍前往平亂,殉難者後來也安葬於原義民塚旁,是為附塚。盛大的葬禮後,「同治四年,林劉施主爰集聯庄紳土,選舉管理,坤等將契券交管理人權放,其管理者三年一任為限,限滿仍將契券交出施主點交新管理人領收清楚。此乃四庄輪終而復始,為管理者自當秉公妥理,日後嘗祀浩大,以增粵人之光矣。……此係通粵之褒忠嘗,有關全粵之大典,各要忠心義氣以經理,不得私自貪圖以肥己也。」[28]竹塹城外居民祭出族群之大纛,讓褒忠嘗成為所有廣東人的褒忠嘗,於是大湖口終於又接任了。
表4 枋寮義民廟輪值經理表
|
年代 |
街庄 |
輪值經理 |
|
1838 |
新埔街 |
金和號、榮和號 |
|
1839 |
新埔街 |
錦和號 |
|
1840 |
新埔街 |
振利號 |
|
1841 |
新埔街 |
榮和號 |
|
1842 |
新埔街 |
雲錦號 |
|
1843 |
新埔街 |
慶和號 |
|
1844 |
新埔街 |
金和號 |
|
1845 |
新埔街 |
錦和號 |
|
1846 |
新埔街 |
榮和號 |
|
1847-1849 |
大湖口庄 |
張阿喜、羅阿水、戴水生、葉阿滿、徐阿恭、吳天寶、陳阿采 |
|
1850-1852 |
石崗仔庄 |
鄭忍吉、劉元勳、葉李妹、□江海、張開旺、陳朝綱、陳山茂 |
|
1853-1856 |
九芎林庄 |
鄭阿茂、詹如海、曾捷勝、林阿請、林阿拿、何茂筠 |
|
1856-1865 |
新埔街 |
劉雲松、范阿裕、行行號、胡永興、朱金振、劉石進 |
|
1865-1868 |
大湖口 |
張阿龍、羅際清、戴朝楨、葉玉成、羅來錦、陳嘉謨 |
|
1868-1870 |
坪林五分埔 |
范嘉鴻、詹萬德、范錦光、朱阿傳、許生淡 |
|
1871-1875 |
九芎林庄 |
鄭家茂、曾清瀾、詹國和、彭殿華、林冠英、彭天祿 |
|
1875-1879 |
新埔街 |
金和號、興隆號、行行號、胡永興、范逢熙 |
|
1879-1882 |
大湖口 |
傅合源、周三合、黃惇仁、張裕光 |
|
1882-1888 |
五分埔 |
劉錦標、詹崇珍、劉廷章、朱洪浩 |
|
1882-1883 |
九芎林 |
劉如棟、劉正記、鄭紹周、林上華 |
|
1883-1894 |
新埔街 |
潘金和、范逢膝、蔡景熙、蘇義利、范振茂 |
|
1894- |
大湖口 |
徐景福、傅萬福、張坤和 |
資料來源:《褒忠義民廟祀典簿》及《林施主收執簿》,轉引自賴玉玲2001:242-243。
外庄經理人概念帶領義民廟走過日漸繁榮的十九世紀後半期,留下了虎邊中路的三位原經理祿位;外庄經理制度甚至讓義民廟熬過廟燬於倥傯兵馬,順利重建後,也留下了虎邊右路的三位重建經理的祿位。然而外庄經理人制度卻也同時造成經理人日漸擴權,凌駕施主之弊端。明治三十二年至三十八年(1899-1905)日本政府先後公布「依舊慣之社寺廟宇建立廢合辦法」及「神社寺院及依照本島舊慣寺廟之所屬財產處分辦法」,義民廟應日本政府要求,大正三年(1914)相關街庄商議組織「義民廟協議會」,並制定「義民廟協議會規約」,廟務之經理至此的進入了管理委員會的時代,由選自祭典區十四大庄的管理委員,互選出管理人。
這一轉變的重大意義在於十九世紀的雙元組織體系至此結束,廟產經理回歸祀典爐主,成為一元體制。不過這一轉變持續了二十年才完成,「枋寮義民廟協議會委員及管理人選舉規程」於昭和十年(1935)通過,限定委員之資格,林、劉施主為直系遺族,各祭典區則為最近期輪值祭典之調首或遺族。民國三十六年(1947)協議會改組成「褒忠義民廟管理委員會」時,仍繼承這一傳統,且一直沿襲至今。這一轉變的影響是爐主制度跟著發生重大變革,由於管理委員的資格被限定,等同於限定了十四大庄之爐主資格。至此義民廟的管理委員及各大庄爐主合一,而且固定由同一宗族的成員世襲接任。
七、調位
關於枋寮義民廟早期的祀典制度最大的線索也來自前述四姓規約,這一制度可以稱為「爐主首事制」。依四姓規約,義民廟建成之後,隨即採行爐主首事制度。早期義民廟文書的立約人皆見「首事王廷昌、黃宗旺、吳立貴及林先坤」等字樣,首事,即董事的別名,首為起首之意,近似所謂發起人。首事原有其鄉治上的意義,如河南長葛縣「向設公議局,由各保首事組織。民國成立,趨重議會,首事名稱已不適用。嗣因某議會奉命解散,合邑公務幾無要領。因設董事辦事處,各董事輪流交替辦公」[29]。然而,首事在承辦祭典上亦有其意義。例如,張汝誠所輯《家禮會通》對春秋里社鄉社之祭有深入的描述:城市鄉村逢春秋二社日,各處祀五土五榖神,以盡春祈秋報之禮,禮稱報賽,俗云「做福」。輪當首事,潔壇場、具牲禮。先日,會首及與祭者,齋戒沐浴,設位(五土居中、五榖居西)牲案香案居中。
依四姓規約文字「爐主及首事四姓輪流祭祀之日,當具告白字通知粵庄眾紳士,前來與祭。現年爐主及首事要辦祭費,仍長銀項不得私相授受,無論多少當眾交出」文中所指首事即為承辦祭典人之職稱。目前的文獻資料已無法查考四姓輪值爐主的實質狀況,不過我們大致可以推斷義民祭典的承辦方式係四姓輪值擔任爐主,未輪值者則為首事,協助爐主。因此,我們大致上可以認定當時的祭典組織是爐主、首事二層制。
到底當時承辦祭典的情形如何?四姓規約提供了一個重要線索:「後日粵庄知四姓辛苦,協力建造塜廟成功,每年祿位開祭,具告白字通知,并立帖請褒忠亭經理人,并七月中元爐主以及大小調緣首等,前來登席。」原本這段話的重點在於預想廟務發展順利的情況下,將可在廟內開祭四姓首事祿位,同時擺席慰勞相關人等。不過,這段文字卻意外地透露了七月中元祭典的相關人員,他們是爐主、大調、小調及緣首。更令人興奮的是,我們在一百年後的一張「調單」上,居然可以清楚地解讀這種三層制的祭典工作人員。
枋寮義民廟所謂調單即慶讚中元祭典的主事人員分工表,目前枋寮義民廟尚存最早的調單為明治四十二年(1909)當年值年的坪林石崗仔聯庄為「褒忠亭慶讚中元」祭典所印製(以下簡稱1909年調單)。[30]調單上列滿頭銜與名字,以1909年調單為例,包含三十四個頭銜,二百三十二個名字。這三十四個頭銜,可以區分成三個層級,即爐主、調與緣首(參見表五)。
表5 新竹枋寮義民廟西元1909年調單職稱表
|
層級 |
類別 |
頭
銜 |
|
一 |
爐主 |
總正爐主、總副爐主、爐主 |
|
二 |
調 |
總主會、總主醮、總主壇、總主普、總總理、總經理 |
|
正主會、正主醮、正主壇、正主普、正總理、正經理 |
||
|
副主會、副主醮、副主壇、副主普、副總理、副經理 |
||
|
三 |
緣首 |
總緣首、五谷首、大士首、司命首、城隍首、三官首、福德首、觀音首、褒忠首、水燈首、協贊首、燈篙首、都副首 |
資料來源:抄錄並整理自劉澤民 2003:249。
爐主係祭典的負責人;調是事務性分組;緣首即斗燈首,是斗燈的贊助者。這樣的祭典分工體系其實不是特例,而是台灣醮儀中大同小異的分工模式,而且也大致上一直沿用至今。台灣民間建醮祭典時會設立醮壇組織,組識成員以斗燈柱首為主體,其最高職位設總經理一人,即等於醮主;並設經理若干人,另設爐主數人。
其次是主會、主醮、主壇、主普等所謂四大柱(相關論述請參考劉枝萬
1983;劉還月 1994;黃文博 1997;李豐楙 1998)。四大柱原本應是醮務的核心,主會是各壇之總監督;主醮是督導道士,負責祭典科儀者;主壇負責辦理祭壇之設與清除事項;主普則是負責普渡,辦理普施賑濟(劉澤民
2003:248)。在各地醮典的四大柱中,通常會再分化兩層為頂四柱與下四柱,甚至如1909年調單所示,分化為三層,可以稱為頂四柱、下四柱與外四柱。由於閩語「柱」讀如客語「調」(tiao),因此客家乃用調字稱柱,醮務分工單乃因之稱為調單(tiao dan)。
緣首與首事之意同,經過卜筊,有緣方可為首事。[31]大部分地區都稱打醮時侍奉神明的代表為「緣首」,緣首是在打醮儀式進行時,代表「闔鄉醮信人等」拜神的人。他們在神前被選出,在打醮的大部分儀式中代表鄉民侍奉諸神明。侍奉的方式即為敬獻「斗燈」,所以這些首事也被稱作斗燈首,亦即負責斗燈的人。斗燈是斗與燈的結合,斗即星斗,是人間生命的象徵。儀式中以米斗內盛白米,並放古銅鏡、古劍、小秤、剪刀、尺、紙製涼傘,並點燃煤油燈。
本文認為爐主、調、緣首三層制,可以視為是爐主首事二層制的變形。主會、主醮、主壇、主普實際上就是整個醮典的分工體系,是祭典系統內部分化出來的事務系統。也就是說,爐主與緣首是儀典性的分工,調則是事務性的分工,二者合作完成一次醮祭。目前調(柱)層級在台灣地區的醮儀基本上仍然存在,只是地位有非常大的差別,某些地區依然是核心,某些轉化為地域性輪值單位,某些只是單純的斗燈首。即使是斗燈首,某些地方調(柱)仍具重要地位,某些則已經被邊緣化,甚至已無關輕重。
比較1909年調單至今日之調單,其三層制結構大致存在,但是呈現首尾擴張,中層萎縮的態勢,也就是居中之調(柱)萎縮,而爐主與緣首大幅增加的現象。以民國八十七年楊梅聯庄輪值祭典為例,爐主層級增加副爐主,而由三層變為四層,人數更由大幅擴張至二十九人;調(柱)層級的總、正、副三層制則僅餘總級一層;斗燈首則由十三種增加為十八種(參考表六)。表面上看來,義民廟祭典組織的變革歷史,前期從爐主、首事二層制擴張至爐主、調、首三層次,顯示祭典中事務系統的重要性提高;後期則中層調(柱)的萎縮。然而調(柱)系統的萎縮不但不是事務系統的萎縮,反而是事務系統的擴大,因為事務系統不斷擴大到獨立於祭典系統,而另行成立與祭典系統平行的事務系統。於是祭典時便出現兩種屬性的組織:事務系統的醮局組織與儀式系統的醮壇組織。
|
表6
民國八十七年褒忠義民節楊梅聯庄祭典領調調金表 |
||
|
調 別 |
調
金 |
備 註 |
|
總正爐主 |
60,000 |
固定由陳泰春認領 |
|
總副爐主 |
50,000 |
固定由彭泰和認領 |
|
正爐主 |
35,000 |
全部由十三位祭典委員認領 |
|
副爐主 |
30,000 |
全部由十四位祭典委員認領 |
|
總主會 |
20,000 |
|
|
總主醮 |
16,000 |
|
|
總主壇 |
12,000 |
|
|
總主普 |
10,000 |
|
|
總總理 |
8,000 |
|
|
總經理 |
6,000 |
|
|
經理 |
5,000 |
|
|
各斗燈首 |
3,000 |
計玉皇首等十八種 |
|
資料來源:褒忠義民節楊梅祭典會 1998 「褒忠義民節輪值楊聯庄祭典調別調金表」,轉引自賴玉玲 2001:220。 |
||
目前枋寮義民廟的中元祭典組織正是區分成這兩大系統,事務系統方面有「祭典委員分工小組」,由總爐主自行籌設組成;儀式系統方面的爐主至斗燈首等頭銜,則由庄民以領調(liang tiao)的方式組成。所謂領調指的是認捐贊助經費,至於各項儀式率由事務組織代辦。以輪值八十七年義民廟中元祭典的楊梅聯庄為例,調金從新台幣六萬到三千不等,當年計領出一千四百二十五調,總調金高達一千餘萬(賴玉玲
2001:225)。
醮典組織原本是係臨時性組織,但是枋寮義民廟卻使它固定下來,每年輪值大庄經辦中元祭典時,都用這樣的分工模式辦理,而且如前文所言,不同於一般廟宇以神意決定爐主,枋寮義民廟的爐主是固定的,參與領調者之宗族公號或姓名也會印在大紅的調單上,而且複印給所有領調者,高高的貼在牆壁上,正彷彿廟裡的祿位一般。因此,相對於牌位階序的神位與祿位的區分,本文將爐主以下的名銜階序稱呼為「調位」,意即調單上的位置。
關於調位系統尚有引人注意者,即調位上的名份並非個人,而是宗族「公號」。義民廟各大庄的輪值爐主是固定的,並不開放給所有庄民。目前輪祀義民廟的十五大庄的值年總爐主分別為:六家大庄的林貞吉、下山大庄的鄭振先、九芎林大庄的曾捷勝、大隘大庄的姜義豐、枋寮大庄的林六合、新埔大庄的潘金和、五分埔大庄的陳茂源、石岡仔大庄的范盛記、關西大庄的羅祿富、大茅埔大庄的吳廖三和、湖口大庄的張六和、楊梅大庄的陳泰春、新屋大庄的許合興、觀音大庄的黃益興、溪南大庄的徐國和。這些爐主都是宗族,無一例外。宗族的公號除第一字為姓氏外,第二字多為數字,依其宗族房份而定;第三字或第二、三字則冠以「興」「芳」「和」「泰」「昌」等吉祥字,象徵宗族同心合力、家道興隆。不但十五大庄總爐主為公號,即使單一大庄內的各總正副爐主也幾乎都是宗族,以民國八十六年(1997)湖口大庄為例,張六和、羅合和、周三合、傅合源、陳四昌、張昆和、吳義昌、戴拾和、林長泰、陳榮和、黃六成、范國茂等十二個各級爐主全為公號(邱彥貴 2001:159-160)。即使爐主以下的大小調與緣首,也幾乎都是公號,以前引1909年調單中的陳姓為例,總主會陳三煥、總總理陳四興、陳九和正爐主陳鼎芳、副爐主陳騰芳、正主醮陳和昌、正主普陳來興、副主壇陳達和等也都是公號(劉澤民 2003:248-249)。換言之,整個調位階序都由宗族所組成,而宗族又是本地的主宰力量,這更加顯示調位階序之存在的重要性。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緣首並非祭典體系的底層,真正的底層一直延伸到家戶,而完成這一工作的是奉飯制度。義民爺祭典除了當天最受人矚目的儀式之外,整個七月期間輪值大庄內,所有家戶以鄰里為單位,輪流每天舉行「奉飯」儀式。早期係以扁擔米籮直接挑至枋寮義民廟,奉飯義民爺。所謂奉飯無非請義民廟吃飯的意思,祭品就是日常烹調的食物。據傳日據時代,義民廟因皇民化運動而被壓抑,於是家戶轉用自行在家奉飯的方式祭祀義民爺。近年可能是受到媽姐遶境儀式的影響,義民爺被請到當地主廟,直接就近接受庄民奉飯。以民國八十六年湖口聯庄輪值義民祭典為例,當年
八、階序體系的形成
枋寮義民信仰創造了一個包含神位、祿位與調位的階序體系,這一體系以義民神位為核心,將捐施與經理廟產有功者的祿位與祭典區內所有信徒的調位收納為一。這個體系的原動力是竹塹城外居民無主的恐慌,而決定階序高低的因素是財產的捐施與管理,但是國家卻因其封神的權力高坐頂端,也因此將信仰帶來族群的異音。
枋寮義民廟這一階序體係始於無主的恐慌,而其擴大亦因無主的恐慌,因此無主的恐慌可以視為體系的原動力。這種恐慌有兩種形式,一為對別人無主而生的恐慌,一為對自己無主所致之恐慌,而這兩種恐慌在義民廟史裡,最後同時匯注於那場最初的恐慌,亦即對於林爽文役殉難者的恐慌。對治無主恐慌之道唯有使亡者有主,亦即將抽象的亡魂具象為神主牌,有了神主牌才能夠接受祭儀,安享蒸禋。為了安奉這方神主牌,勢必捐施土地產業以營造一處神聖空間,其後再階序性地切割神聖空間,讓捐施者得到祿位牌及神聖空間。於是受捐者不再無主,捐施者也因此而有主。猶有進者,神聖空間的形式不僅包含廟宇、神位與祿位,祭典組織裡的調單也逐漸被視為一種神聖空間形式。透過大量的文字印刷,紅色醒目的調單,從廟宇到家戶的牆壁上,調單上所有的名銜也彷彿成了具體而微的祿位。因此,藉由神聖空間的創造及分割,同時賦予階序,使得眾人皆有主,此即枋寮義民信仰之奧秘。
至於更廣大的超自然世界裡無數無主又無人聞問的亡魂如何而能有主呢?那就依靠年復一年的普渡了!每至七月,竹篙高豎,招請所有水陸亡魂安享蒸禋,讓無主的恐慌得到短暫但卻是週期性的安慰。值得注意的是,義民信仰的昌榮正是因為十五大庄輪值參與義民廟普渡的結果。所以說,義民信仰的興旺係因外庄年復一年參與普渡亡魂的結果,而非義民信仰本身。
我們確實可以相信老邁的王尚武捐出畢生積蓄,只為換得堂上木主一方;我們也可以相信那年四姓首事捐資購得香燈之地,又定頒規約,拈出外庄經理與外庄領調二憲章,亦僅深盼四姓祿位早日開祭。然而無主的恐慌卻無法勾勒義民信仰的全幅樣貌,因為這個信仰自始就與帝國糾絞在一起。
當年帝國四塊匾額分贈四籍人群,固然顯露其族群政治之陰險詭詐,然而將那方本應懸掛通衢要道的褒忠坊牌,改懸於廟宇高樑之上的人畢竟是四姓首事,捐施田產祭祀聖旨與殉城官員也是四姓首事。菁英份子對國家力量的操弄,確實拐彎抹角地將幾乎成為無主亡魂的義民,提升為具有神格的神靈。擁有神位後的義民,不再恐慌,而竹塹城外的居民對殉難者的恐慌也轉為崇敬。於是原本普同於人性的無主恐慌,卻在帝國忠義的匾額下,得到一時的撫慰。原本褒忠與旌義都相同的是帝國對勤於國事者忠義精神的褒揚,然而褒忠就是褒忠,終究不是旌義,枋寮義民信仰就這樣不自覺地捲入族群紛爭之中。一甲子後,同治元年(1862)戴潮春之亂發生,相同的故事帶來相同的殉難者,也相同地葬在同一塊墳地中。我們已經看不到普同人性的無主恐慌,代之而起的是族群的呼喚:「為管理者自當秉公妥理,日後嘗祀浩大,以增粵人之光矣……此係通粵之褒忠嘗,有關全粵之大典,各要忠心義氣以經理……」。
國家以及族群異音的出現,提醒我們義民廟階序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原則,它被財產所決定,但是財產以外的因素,一樣不停地撼動乃至襲奪這一階序。從四姓首事到林劉施主、從外庄主調到固定爐主制,那是撼動;而高舉族群大旗的國家或行動者直接襲奪了這一階序後,王尚武的無主恐慌早被淘盡於歷史長河。唯此係後話,也是另一篇文章。
參考書目
Watson, J. L., 1985, “Standardizing the God: 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 (Empress of Heaven) along the
尹章義,1999,〈閩粵移民的協合與對立:客屬潮州人開發台北與新莊三山國王廟的興衰史〉。頁349-380,收錄於尹章義著《台灣開發史研究》。台北:聯經。
吳學明,1998,《頭前溪上游開墾史暨史料彙編》。新竹:縣文化中心。
李露露,1994,《媽祖信仰》。北京:學苑。
杜鴻賓等,1975,《長葛縣志》。臺北:中國地方文獻學會。
卓克華,1996,〈新埤鄉建功庄建制考〉。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刊二卷四期及三卷一期:98-106。
林尹、高明,1973,《中文大辭典》,第一冊,第455頁。台北:華岡。
林光華及莊英章,「枋寮敕封粵東義民廟古文書」,未出版。
邱彥貴,1993,〈粵東三山國王信仰的分布與信仰的族群:從三山國王是台灣客屬的特有信仰論起〉。東方宗教研究第三期:107-146。
邱彥貴,2001,〈從祭典儀式看北台灣義民信仰:以枋寮義民廟褒忠亭丁丑年湖口聯庄值年中元為例〉。頁150-185,收錄於鍾仁嫻編《義民心鄉土情》。竹北:新竹縣文化局。
桃園縣觀音鄉志編纂委員會編,1986,《觀音鄉志》。桃園:觀音鄉公所。
張
珣,2003,〈台灣媽祖研究新思維:文化媽祖研究的新取向〉。頁109-142,收錄於張珣等編《台灣本土宗教研究的新視野和新思維》。台北:南天。
張炎憲,1998,《竹塹古文書》。新竹:新竹市文化局。
許石井,1989,《北港鎮志》。雲林:北港鎮公所。
郭維雄,2002,〈屏東縣新埤鄉建功庄褒忠門在六堆客家移民開發史上的研究價值〉。發表於「兩岸客家歷史文化社區研究會」,苗栗:苗栗縣文化局。
郭薰風主修,1983,《桃園縣志》。臺北:成文。
陳春聲,1996,〈三山國王信仰與台灣移民社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第八十期:61-114。
黃宗智,1998,《民事審判與民間調解:清代的表達與實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黃貽徐編,1971,《黃姓族譜》。未出版。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1964,《臺案彙錄庚集》。電子資料庫臺灣文獻叢刊第200種。臺北:聯合百科電子。
劉澤民,2003,《關西坪林范家古文書集》。南投:台灣文獻館。
鄭玄,1981,《禮記鄭注》(宋朝余氏萬卷堂校刊本)。台北:學海。
鄭鵬雲、曾逢辰,1898,《新竹縣志初稿》。電子資料庫臺灣文獻叢刊第61種。臺北:聯合百科電子。
賴玉玲,2001,〈新埔枋寮義民爺信仰與地方社會的發展〉。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駱靜山,2002,〈檳城華人宗教的今昔〉,發表於「檳榔嶼華人事跡國際學術研討會」,1月5-6日,馬來西亞:檳城。
魏淑貞,1994,《台灣廟宇文化大系:保生大帝》。台北:自立晚報。
羅烈師,2001,〈竹塹客家地方社會結構的拱頂石〉。頁136-149,收錄於鍾仁嫻編《義民心鄉土情》。竹北:新竹縣文化局。
羅景川,1994,《大樹鄉民間鄉土誌》。高雄:大樹鄉公所。
羅景輝,「湖口羅家古文書」,未出版。
*作者羅烈師,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交通大學客家學院助理授授,e-mail:sii.lsl@gmail.com
。本文首次發表於2004年中研究民族所「階序與權力」學術研討會,感謝謝繼昌、林開世、陳文德、黃應貴及黃
[1] 本文不討論義民神格的問題,而關注於神格認知背後的心理恐慌。至於義民與孤魂野鬼之相關爭議請參考林光華2001〈他們有主!〉,刊於鍾仁嫻編《義民心鄉土情》,頁2-4。新竹:新竹縣文化局。
[2] 依許慎《說文解字》「主,鐙主火主也。」轉引自林尹、高明
1973《中文大辭典》,第一冊,第455頁。台北:華岡。
[3] 例如<周禮地官大司徒>「樹之田主」,注:田神后土田正之所所依也;<周禮春官司巫>「則共匰主」,注:主,謂木主也;<穀梁文二>為僖公主也,注:主,蓋神之所馮依,其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史記伯夷列傳>「武王載木主而東征」。以上皆轉引自中文大辭典,參考前註。
[4] 參考《新竹縣志初稿》,頁186-187。
[5] 參見<羅鵬申道光十一年家書>,收於羅景輝收藏之「湖口羅家古文書」,未出版。
[6] 不著撰者,年代不詳,<四庄建醮序>,收於羅景輝收藏之「湖口羅家古文書」,未出版。雖然這一文本並未註記年代,但是依共同保存的文本的年代,大致可以推斷此一文本應為十九世紀中期之作。
[7] 引自義民廟古文書,嘉慶七年(1802)褒忠亭首事王廷昌、黃宗旺、林先坤、吳立貴等<同立合議規條簿約字>,詳下文。底線為筆者所加,以下同。本文所引用之義民廟古文書係林光華及莊英章所提供,目前尚未出版,以下不贅述。
[8] 引自義民廟古文書,<粵東總理林先坤、姜安,首事梁元魁、鍾金烙、賴元麟、徐英鵬仝立合約字>,下線為筆者所加。
[9] 戴元玖並未隨其子禮成兄弟等來台,禮成兄弟捐地時元玖尚健在,故禮成兄弟以元玖之名捐地,讓元玖生前即享祿位。
[10] 王尚武託孤字並非特例,臨終前將未成年子女託付親友,固然是漢人一般慣例,但是全無子女,而請族人代管產業,以為香火之資,亦常有之舉。因此,託孤的意義在於香火祭祀,也往往與產業之託管互為表裡。
[11] 乾隆五十六年(1791)〈王尚武託孤字〉,轉引自賴玉玲 2001:22。
[12] 乾隆五十六年(1791)正是九芎林佃首姜勝智開始拓墾新竹縣九芎林地區之時,現存古文書顯示,姜勝智招佃墾耕的土地計一百五十
[13] 參考<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十二日上諭>,《臺案彙錄庚集》,頁793-794。電子資料庫臺灣文獻叢刊第200種。臺北:聯合百科電子。
[14] 引自《禮記鄭注》(宋朝余氏萬卷堂校刊本),頁593-594。台北:學海。
[15] 參考許石井1989《北港鎮志》雲林:北港鎮公所;羅景川1994《大樹鄉民間鄉土誌》高雄縣:大樹鄉公所。
[16] 同註7。
[17] 所謂村落領袖即王廷昌等四姓首事,詳見下文。
[18] 關於廟產之經理詳見下文。
[19] 所謂轉火(zhuong fuo)指的是香爐重新登龕座之意,轉即回返之意,火即香火。與轉火相反的概念是出火(cut fuo),即香爐因故離開龕座之意。
[20] 本傳說筆者於2004年六月採訪自湖口戴拾和宗族後代戴國志先生於其住宅口述。其實戴國志並不清楚戴、林之爭發生之年代,僅表示事情發生於義民廟祿位牌轉火之時,且戴雅發先生正是活躍於日據時期,因此筆者依此推測兩姓相爭係發生於明治三十七年(1904)重建完成之時。此外,又依桃園《桃園縣志》〈人物志〉、《觀音鄉志》〈人物志〉及觀音鄉《黃姓族譜》中,都提到觀音士紳黃雲中曾於咸豐三年(1853)時,調停枋寮義民廟戴林兩施主關於廟址及奉祀問題的爭議。或許戴林之間長期爭議,也或許戴國志口述之故事正是1853年黃雲中所調停之爭議,目前尚無答案,不過無論如何,戴林之間關於祿位階序之間的緊張關係確屬事實。而這也莫怪乎戴氏宗族特別將當年戴元玖施地之合約字全文刊於族譜中,並且用粗體大字強調捐施義民廟地是歷史事實。
[21] 引自義民廟古文書,同治四年(1865)<褒忠廟記>。
[22] 同註12
[23] 參考義民廟古文書,嘉慶七年(1802)四姓首事<仝立合議規條簿約字>,部份文字之下線係筆者所加。
[24] 嘉慶七年十月周龍章立杜賣盡根田契。
[25] 雖然此時義民廟尚未有「經理人」這一職稱,但依本四姓規約,經理人的觀念已被提及,詳見下文。
[26] 林施主收執簿14-15頁,轉引自
[27] 引自「義民廟古文書」,道光二十七年(1847)<林茂堂等請帖>。
[28] 引自〈義民廟記〉,見於「義民廟古文書」。
[29] 陳鴻疇修《長葛縣志.卷三政務志》,「董事處」(台北:中國地方文獻學會,1976),頁104。另外,黃宗智(1998)從直隸寶坻縣衙舊檔案中亦見牌頭、甲長和首事等村級領袖。
[30] 此褒忠亭即枋寮義民廟之舊稱。
[31] 例如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香光寺設爐主、緣首(墨明<誰傳「大媽」的旨意?> 香光莊嚴49,1997);竹南五穀宮重建碑亦載:同治十三年(1874),已歷七十餘載,其壁傾瓦頹,樑柱腐朽,遂由中港庄五品軍功頂戴陳紹熙為總理,林呈祥為經理,徐琳盛、陳漢雲、劉錦章為緣首,發起募捐,重修廟宇。嘉慶五年(1800)的創建和道光四年(1824)的重建,青雲亭的領袖蔡士章和梁美吉都分別名列緣首,後者還擔任那一年的董事。馬來西亞檳城1824年的《重建廣福宮碑記》署名亦見緣首頭銜,轉引自駱靜山2002<檳城華人宗教的今昔>,「檳榔嶼華人事跡」學術研討會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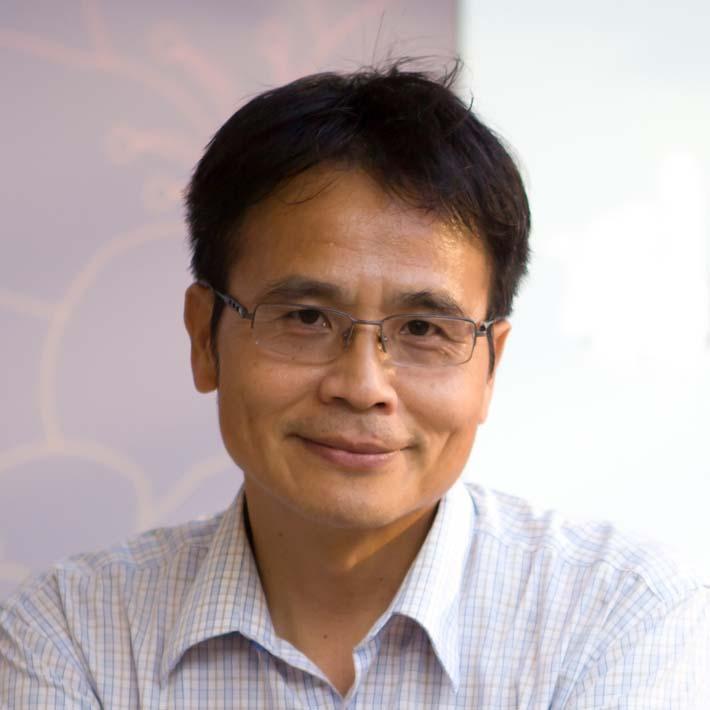

0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