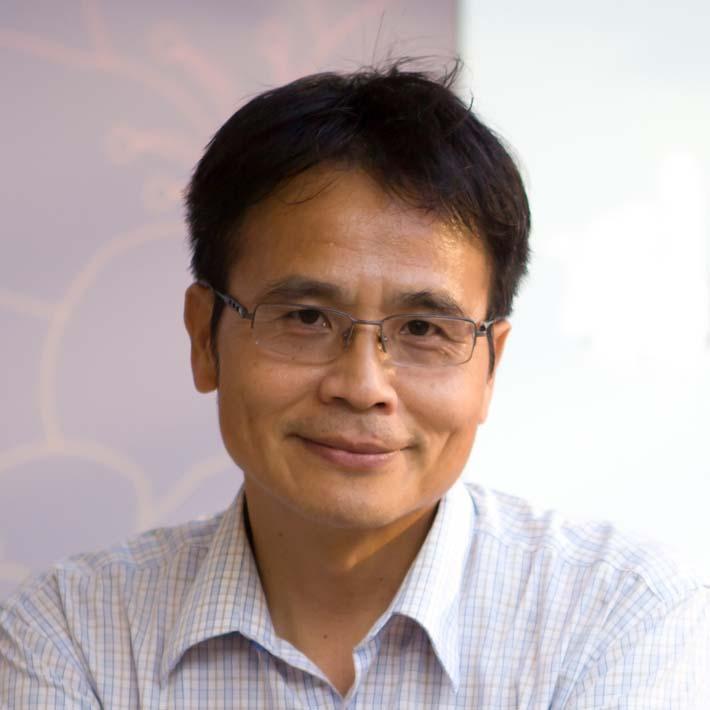通往地獄的天堂之路:道卡斯竹塹社文化之殞落
羅烈師
清華大學人類所[1]
給地、賜姓與封官表面上是統治者賦予原住民無限的尊榮,然而享有這一尊榮,卻導致道卡斯竹塹社人喪失其傳統社會文化,更進而族群泯沒而不自知。路彷彿天堂,盡頭卻是地獄。
衰落的竹塹社
道卡斯族竹塹社和臺灣其他平埔族人一樣,從荷蘭據臺時期以來,已經消失或漢化,除非是專門研究這問題的學者,一般人已經無從知道目前尚存的平埔族之所在了(陳其南 1990:5)。竹塹社文化業已殞落,社會結構亦告瓦解,僅竹塹社人倖存。以漢化一詞自然不足以全幅彰顯竹塹社人社會文化變遷的過程,因為這個詞語犯了漢族中心主義的毛病,而且蒙蔽了漢人的「平埔化」現象。然而無論如何,在現今社會我們已經找不到一個操道卡斯語的竹塹社人,所謂「竹塹社」早已成為歷史名詞,它充其量只在研究者間流動。[2]
清治時期是竹塹社社會文化變遷最劇烈的時期,這段歷史中有三件最緊要的事:給地、賜姓、與封官。這三件事化從生產模式的轉型開始;進一步改變財產及繼承的觀念;最後終底於瓦解竹塹社的社會結構。自此竹塹社文化成了無根的文化,而逐漸凋零,客家文化順勢取而代之。雖然竹塹社人沒有消失,只是這個族群已不再馳騁鹿場,也遺忘祖先的語言一百年以上。
文獻回顧
社會文化變遷是目前平埔研究的焦點,關於竹塹社的研究亦然。這些研究注意到作為主要生產工具的土地(黃富三 1981、施添福 1990、邵式伯
1993、張炎憲、李季樺 1995、王世慶、李季樺 1995)、家族的形成與變遷(張炎憲、李季樺 1995)、及儀式行為的社會物質基礎(王世慶、李季樺 1995)。這些研究都共同的重視土地所有權課題,但是分別從經濟、社會、宗教等進路,探討竹塹社之社會文化變遷這一母題。茲分述如下:
黃富三、施添福、邵式伯:三個人同時都關心土地所有權轉移的問題。黃富三認為平埔族人杜賣草地或出售、出贈、出典田野的原因是經濟壓力、無力自墾、生產力低、以及漢人佔墾之威脅(黃富三 1981:78-79)。
施添福認為竹塹地區平埔族人失去土地的原因是清帝國的統治方式造成的。竹塹社人並非不諳耕作,只是缺乏一個「力農環境」,所以頻頻杜賣土地,以致無由建立農耕社會。雍正朝十餘年間,竹塹地區土牛溝以西的熟番草地,幾乎大部份皆落入漢人的手中。此時平埔族之所以紛紛杜賣草地的二項因素是:其一、課餉、花紅陃規及其他雜派需索繁重,相對的其賴以納餉之鹿場漸小,鹿產漸少;其二、勞役供差繁多,使竹塹社人居無寧日。至於乾隆中期之後竹塹社人杜賣田園,則是因為社人不斷被迫服國家勞役。自乾隆初年以來,隨著竹塹地區進入積極開發階段,為防止生番逸出為害,只有不斷派撥熟番。先是沿著土牛溝的番界,後是沿著養贍埔地邊緣的番界充當隘丁。全臺番丁有幾?去其壯丁四千,且兩年一換,分扼山內生番,則全臺社番番社,不解體者亦難矣(施添福 1990:71-87)。
邵式伯認為臺灣是清政府的邊疆之一,對臺之統治方式,自然就是清政府邊政之一環,清之邊政是由「戰略意義」(strategic significance)、「控管成本」(control cost)、與「稅收效益」(revenue potential)」三項原則共同決定的。領臺之初,清政府以平埔族為課稅對象,故實施海禁,隔離漢人之侵擾,以確保臺地平埔族之地權,同時確保其稅收。偷渡人口大幅成長後,衝突昇高,迫使政府設官直接治理,控管成本乃隨之增加。一旦直接設立行政組織後,為維持此一組織,必須在財政上的能夠自給自足。為達成此一目的,唯有增加報陞已墾土地,同時鼓勵更多的漢人入墾。此一政策撼動了平埔族對未墾土地的所有權。而多重地權的現象,便在政府、平埔族與漢族的互動關係下形成了。簡言之,平埔族的土地權力,其實是被清政府之邊政決定的。在增加稅收以維持常設治理機關的要求下,平埔族的地權自然就被剝奪了(Shepherd 1993:1-24,395-410)。這意謂平埔族的土地所有權是清政府所賦予的,後來也是被清政府所剝奪的,而予奪之間,是政府基於邊政的稅收考量。
施添福與邵式伯分別從微觀與鉅觀角度審視平埔地權的喪失,二人的結論一致指向政府的統治態度。只是前者的焦點是平埔社人的勞動力,後者的焦點是治臺政府的稅收。
除了土地權益的喪失造成竹塹社衰退之外,其他的原因包括:內部派系鬥爭與侵吞社租屯餉、婚姻與族群歷史文化記憶的喪失等(張炎憲、李季樺 1995:189-93)。然而竹塹社這個道卡斯族群並未消失,雖然現今竹塹社傳統的祭祖儀式已不復存在,目前的祭祖儀式,無論從祖廟之興建、奉祀之神明與配制、乃至祭祀之形式及祭品等,都已「漢化」。但是透過客家式的竹塹社七姓公派下祭祀公業,竹塹社人以宗族的形式,仍維持其身份與族內團結。甚至其祖廟進一步與在地的客家或閩南信仰結合,成為一個共同的地方信仰(王世慶、李季樺 1995:153-64)。
此種社會變遷的原由是什麼呢?從生產的角度觀察,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方式的定居耕作者,明顯地要一套土地所有制來規範可耕地的使用。同時,假如他們是水田耕作者,還需要一套複雜的水利管理體系(Lewis 1985:200)。這一套規範與管理體系用新馬克思主義理論者的術語,就是一套生產模式;或者用比較模糊、比較容易被英國色彩的社會人類學者所接受、也是馬克思常用的術語:社會形構(social formation)。馬克思主義者的社會科學有三個基本分析進路:整體觀點(holistic)、歷史觀點(historical)、與生產觀點(production-oriented)。所謂整體觀點是指吾人在分析社會制度時,係檢視經濟、社會、觀念、政治等力量的互動關係;所謂歷史觀點是指馬克思主義者相信自己對社會制度的解釋是最完備的,因為它足以說明社會制度形成的原因,畢竟社會制度是在一特定時空下運作的;所謂生產觀點是指馬克思主義者假定人類最基本的活動是「社會勞動力」,也就是指人類以一套有組織的行動模式,自環境中取得能量以再生產社會自身(Plattner 1989:380-1)。正因這三個觀點,使得「辯證法」(dialectics)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所關切的分析方法。
從上述這一角度思考,筆者以為前述關於竹塹社人的研究可以整合為一套模式,共同描述竹塹社人所面臨劇烈社會變遷的過程。實際上,此一構想在巴則海族(Pazeh)的研究中已有提及,然而此一構想仍停留在未來研究的課題與觀點上,並末實際的展開(張隆志 1991:260-265)。[3]而且更重要的是,諸課題與觀點之間的所共同形成一體系,也未被強調。因此本文以這一整體模式,思考竹塹社社會文化的變遷。
竹塹社社會文化的變遷:得而復失的土地所有權
臺灣的南島語「原住民」,依日本學者的研究,分成「高山族」與「平埔族」。[4]其中高山族共十族,分佈於中央山脈;平埔族則有十二族,活動於西部及東北部沿海平原。[5]關於臺灣北部的平埔族活動範圍,北部沿海是巴賽族,臺北盆地與桃園臺地屬於凱達格蘭族,宜蘭地區為噶瑪蘭族,新竹與苖栗是道卡斯族,臺中平原則為巴則海族。高山族方面,泰雅族在北臺灣中央山脈活動,新竹東南山區則有賽夏族。
竹塹社住民原分佈於香山一帶,鹽水港附近,後逐漸往東北移動。1722年(雍正元年)設淡水廳,廳治設於竹塹,並於1733年築城。帝國所選定的城址正是竹塹社住民居所,於是住民被迫遷往舊社。隨後復因水患,於1749(乾隆十四年)年,由舊社舉族遷往新社、枋寮等處移墾,且向西往新埔關西發展。其活動範圍,西南至鹽水港與中港社相對,東至咸菜棚、龍岡及楊梅壢、中壢間的土牛與南崁社為界(張炎憲,1995:174)。
從社會經濟的角度觀察,整個平埔族的歷史經過兩次重大變革。第一次變革是荷蘭人引入的鹿皮貿易與樸社制度,第二次則是中國華南式水稻生產農業及地權制度之引介(張隆志 1990:261)。第二次變革同時也是生產技術的變革,較諸前者更深更廣的改變了平埔族人的生活,本文亦置重點於此。
平埔族的傳統生活方式為遊耕(horticulture)與狩獵。所謂遊耕是指耕作者在土地、勞力、資金、及器械等生產要素方面都顯得較為疏放,他們以鋤頭或掘棒種植作物,土地不是固定的財產,也稱作燒墾耕作,以砍伐及焚燒的方式清除土地上的樹叢或雜草(Kottak 1997:219)。此種農耕方式至荷蘭人統治臺灣期間產生變化,荷蘭人設專司機構掌管牛隻的馴養,作為耕作及曳引之工具。
荷蘭時,南北二路設牛頭司,牧放生息,千百成群。犢大設欄摯之,牡則俟其壯,乃漸飼以水草,稍馴狎,閹其外腎令壯,以耕以輓(臺灣府志卷二叢談)。
然而,十七世紀下半葉的這一技術革新,直至十八世紀初期,仍未被竹塹地區採用,當時的竹塹社人仍以鐵鋤及掘棒為農具。同一時期,同為道卡斯族活動於竹塹社南方的中港社人,已有馴養野牛的技術。但是這些野牛只被當作拉車的動力,並非翻土之牽牛。
番丁自昔亦躬耕,鐵鋤掘土僅寸許;百鋤不及一犁深,那得盈甯畜妻子。鹿革為衣不貼身,尺步為裳露雙髀。是處差徭各有幫,竹塹煢煢一社耳。鵲巢忽爾為鳩占,鵲盡無巢鳩焉徙(黃叔璥 1724:135)?
至中港社,見門外一牛甚腯,囚木籠中,俯首跼足,體不得展。社人謂是野牛初就靮,以此馴之。又云:前路竹塹、南崁山中,野牛千百為群,土番能生致之,侯其馴用之。今郡中輓車牛,強半皆是(黃叔璥 1724:133)。
中國華南式水田耕作技術似乎直到十七世紀中期,才正式被採用。西元1742年及1748年霄裡社通事知母六(即蕭那英)在龍潭地區築霄裡大圳,如果「連早期以狩獵為生的竹塹埔北部的霄裡社,都具有開圳的能力,那麼定居於竹塹埔南緣,『其地平坦,極膏腴』的竹塹平原的竹塹社,其從漢佃習得農耕技術之程度,也就不問可知了」(施添福 1990:71)。
關於竹塹社婚姻方式的研究,目前仍停留在假設階段。筆者大膽的猜測竹塹社七姓之間很可能採取「間接交換婚」,從目前整理出來的衛、錢二姓竹塹社族譜,賜姓之後三代內,竹塹社之女人的流向是:潘姓→衛姓→錢姓(參考張炎憲、李季樺 1995:205-215)。這當然只是一個片段的證據,尚待更多資料佐證。而且如果竹塹社也確實存有年齡階層的組織(李亦園 1982:65),那麼竹塹社的社會結構已經呼之欲出了。道卡斯、巴則海、和安雅、貓霧拺等族可能都基於這種交換婚而形年齡組織,而年齡組織又成為社會結構的核心。而其社內事務之處理或許採用「合議制」,「這些村落沒有一個共同的領袖……可能有一個包括十二個最有名譽的委員會。委員任期二年,委員年齡約四十歲,所有委員均屬同年」(戴炎輝 1979:359、李亦園 1982:66)。
竹塹社的土地財產所有權是全社集體制的,而且這一制度至少維持到西元1733年(雍正11年)。這一年竹塹社將相當於現在新竹縣新豐鄉的貓兒椗草地,賣給閩人郭奕榮,其出賣者即由竹塹社土官、甲頭、老番、及白番共同署名。[6]
竹塹社人本來就有全主共同祭祖,謂之「田」。每年三月十六日及十一月十六日,由土目(頭目)具祭品,舂糯米為□,鹿肉、豬肉、雞鴨之屬,皆用生,並酒,置地而祭,呼請其祖先名號。選社中善走者十餘人,鳴金,各以手互相牽引,跳躍同走,旋分手走,漸走漸邊,約走數里,又聚集,以手互相牽引,跳躍一番,再分走十餘里,則各騁足力奮迅如飛,先回到社者受上賞,給以呢、馬掛一件、銅錢二千四百文,其次者賞有差,則各色布疋、碗碟之類,謂之「走田」。然後開罈飲酒為樂,受上賞者未飲,餘人不敢飲。另也於五六七八等月舉行走奠(王世慶、李季樺 1995:133-134、153)。[7]此一祖靈祭的「原始意義實與阿美族、卑南族的入會儀式(成年儀式)相同。然而因為平埔各族漢化已深,其固有宗教習俗大部份已不存在,其僅存的宗教儀式,便揉合了祖靈祭和入會儀式兩種禮儀,一方面保存對祖靈的信仰,一方面保存對少年人各種技能的訓練,便成為今日『賽跑型』祖靈祭的形態」(李亦園 1982: 65)。此外,筆者以為關於祖靈祭儀式這種強調青壯男子的長跑能力,當然與其狩獵生活方式息息相關。
然而漢人農耕文化隨著大批遠超過竹塹社人口數的漢人進入竹塹地區後,竹塹社人的生存開始受到威脅,其社會文化逐步歸於毀滅,而直接的沖激發生在土地所有權上。
如前文獻回顧所述,平埔地權的喪失是其社會文化變遷的關鍵,然而吾人也不應忽略平埔原初土地之取得方式。只有理解竹塹社土地之取得方式,才能理解其失去土地的原因。竹塹社人是竹塹地區的原住民族,早在西元1702年(康熙四十三年)已向清政繳納「番社餉」。對清政府而言,向竹塹社徵稅等於承認他們在竹塹地區生存的權利,也連帶賦予他們土地所有權。從這一角度觀察,竹塹社的土地所有權是清政府憑藉其統治者對土地的最高主權,所賦予竹塹社人的權利。[8]往後所出現的「番大租」權,即源於此。所謂大租權當是與小租權相對而產生的,二者本質上有所差異(陳其南 1990:72)。番大租權的來源是原住民向清政府繳納租稅的結果,小租權則因漢人以資金及勞動力改造土地,增加其農業生產上的附加價值而來。這具體的表現在當時契約上常見的用語「……付與○○○自備工本,前去開築埤圳,招佃墾耕,陞科報課,永為已業。」因此竹塹地區的一田二主(竹塹社人與漢人)不是直接仿自華南,其背後的真正原因是水田耕作相對於狩獵,所需要的大量資本及勞動力的問題。然而這並不意謂竹塹社在清治之初所得到只是所謂番大租權,他們所得到的是全部的權利,只要他們具備資本與勞動力,照常可以擁有小租權。
然而水田耕作必須有相配的社會制度或組織,這是技術、資本、與勞動力之外一個重要因素。水田耕作的命脈是水,因此灌溉系統的興建與維持攸關水稻的生產。十八世紀末期(嘉慶初年),竹塹社通事錢子白及其族人在紅毛港溪上游之四湖溪、北勢溪、波羅汶溪開闢灌溉系統,對遊耕的竹塹社人而言,這無疑是一個偉大的創造。然而錢氏等人只負責陂圳的興築(開圳),至於維護工作(顧陂)則完全由佃戶負責(新竹文獻委員會
1954)。臺灣的河流屬於所謂「荒溪」,流量變率極大,陂圳被大雨沖毀是常事,因此灌溉系統之維護工作所需要的工本,超過興建的工本。更嚴重的是灌溉系統的運作過程中,經常發生耕作者之間用水權糾紛,而且此一糾紛直接威脅整個灌溉系統的維持。茲舉亦為竹塹社地的八張犁為例:
仝立合約人八張犁庄佃友 耕人 等,為重申舊約,立汴除弊,以均灌溉,以安農業事。竊惟弊端不除,則善規難立,本分不守,則家業雖安。緣我庄中二段眾佃友,課田俱賴小三□山泉灌漲。先年屢經業主配立汴缺,自首汴以下分定貳拾伍分半分流,公議申禁,不許私行截塞破挖。奈因年深汴廢,事久約弛。近有無恥之徒,只知私心利己,不照水汴通流,恃勢橫行,違擅舊約。或乘機截破,或暗地挖吼,以致源枯流滯,上有下無,一二滋弊,眾人效尤。苦樂不均,難以盡述。勢得合我十三份半田佃耕人,申請業主前來,照依舊額,新立汴缺,再議規條,重申例禁,杜絕利弊。自約之後,各宜照議而行,庶幾弊除業安,共敦鄉井良規,不失親睦高誼。今欲有憑,仝立合約一樣二紙,付共約首末二汴人,各執一紙存照。 謹將公議規開列
一議□原圳路□迫洪水沖塘,或天旱作□,宜協力修築開導。如違,罰谷三斗,為 福德祠需費。
一議約內谷請一人巡管水源圳路,每全年貼工資谷 石,早晚量交,照汴額水分 派出,不得吝嗇。
一議管水之人來報有人盜水,各宜齊到與他理論。如違,議罰。
一議水路自源達流,從首至尾,不論何人,違汴私偷,捉獲報知,甘賞錢四百文, 絕不食言。(此條寫在下一條)。
一議約內各守本分水額,不得恃強欺弱,偷截破挖。如違,察□公罰佛銀式大元 正。(此條寫在上一條)。
一議管水之人倘因爭水挾嫌,被毆受傷,公眾請醫調治,□□□訟,一切費用均 派。如有臨局推搪延誤者,每元每月照加□□□□□□妥人,當眾擔認,毋私 立限。為憑。
正本請源合同
道 光 十九 年 二 月 初二 日 仝立請帖人佃友 耕人
這張契約顯示,不在庄的地主根本無力維護灌溉系統。從上述契約我們可以得知竹塹地區客家村落維持灌溉系統運作的模式。這套模式所面對的是共同使用灌溉水源的耕作者之間的緊張關係,其模式是全體使用者共同訂定契約結合成法人團體以平均分配水源,這法人團體以福德祠為代表。以財貨僱工巡管圳路,對於違規者施以罰金。如有盜水情事,則全體共同參與談判對抗盜水者。因此,水田耕作中灌溉系統的構築、維護、及運作,不只需要技術、資金、與勞動力,更需要一個社會體制,才能維繫。然而對於竹塹社人而言,這一切是如此陌生。
清廷實施海禁,尚且無法扼止漢人涉險渡臺,竹塹社人更是無法阻擋漢人進入竹塹地區。既然無法像漢人入侵之前那般繼續在整個竹塹地區過著沒有漢人的生活方式,竹塹社人只有面對挑戰,選擇適合的維生之道。面臨生存危機的竹塹社人可以有下列選擇:
a.全面自耕所有土地
b.成為不在庄地主
c.部份土地自耕,其他招漢佃入墾,坐收大租
d.遷徙
竹塹社人口不過千人左右,不可能全面自耕整個竹塹地區。另一可能的作法是成為「不在庄」的地主,然後以招墾或出佃的方式經營土地,坐收大、小租,並且將這些收入轉投資到未墾土地開發或從事商品買賣。然而建構這一不在庄地主階級所需要的陌生知識,恐怕需要更長的時間才可能習得的,對竹塹社人而言,更是遙不可及。何況竹塹社人的對手,閩客兩籍漢人業主,並不給他們這個機會。遷徙是另一個可以維持傳統生活方式的方法,就像巴則海族離開臺中盆地,西拉雅進入後山(李亦園 1982:53-6),竹塹社人也溯鳳山溪求生。然而,事實證明,來自大海的漢人潮水般湧來,不可扼抑,逃無所逃;內山又有賽夏族人窺伺,竹塹社人險象環生。於是唯一的一條路就是守住尚未賣去的田園,以漢人的方式耕水田。於是傳統的土地財產共有制冰消瓦解,竹塹主人開始「分界」「自耕」,保住一方立錐覆瓦之土。
這段土地的歷史不只是取得土地,然後又失去土地而已。嚴重的是,經過這一土地權得而復失的衝擊,竹塹社所失去的不只是一塊土地,而是一整套傳統的社會文化。這一套社會文化原來是竹塹社狩獵遊耕生產模式的一環,竹塹社失去狩獵遊耕的土地,採行水田耕作之後,傳統的社會及文化系統,開始解體。
首先解體的是竹塹社之「社」共同組織。原先之社共同組織的經濟基礎是土地財產權的共有制,各姓分界自耕之後,轉而以已賣土地之大租支應社共同組織之開支。然而竹塹社的大租權受到小租權及佃權不斷移轉及鬮分的影響,越來越不穩定,拖欠抗繳的情況日益嚴重。依賴社租生存的竹塹社共同組織,便面臨日益加深的危機。
婚姻制度也受到挑戰。分界自耕之後,各姓與眾多漢人共居,形成新的村落,新的婚姻圈,傳統的間接交換婚於茲告終。婚姻制度的改變,直接切斷了竹塹社各姓的交換關係,進一步瓦解竹塹社的整體社會結構。
猶有甚者,狩獵遊耕的竹塹社人應付來自華南水田文化的漢人尚且力有未逮,清廷卻又賦予平埔族人重任:屯田制度。西元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發生林爽文事件,福康安率兵渡海,並結和平埔族人,於1788年平定其事。福康安於是擬議以平埔族人設屯,藉以捍衛地方一般治安;防禦未受漢化的南島語族原住民;並供差遣(戴炎輝,1979:467)。屯田制度抽調大量竹塹社勞力,不但使之無法專力於農耕;這些經常離家、離社的男丁,也無力管理家務及社務。
與屯田制同時發生的大事是所謂「賜姓」,即竹塹社接受漢人姓氏(王世慶、李季樺 1995:132)。賜姓的結果,道卡斯人失去了他們的歷史。我們可以想像,沒有文字的道卡斯人,曾經在每一年的「田」祭中,在成年儀式中,族中長老以口傳方式,將道卡斯的神話與歷史故事,代代相傳。賜姓之後,伴隨著其他各社會文化層面的變革,民族的早期記憶幾乎完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漢人的族譜,而且這種族譜僅及賜姓之後。於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大甲至雞籠,諸『番』生齒漸衰,村墟零落。其居處、飲食、婚嫁、喪葬、器用之類,半從漢俗。即諳通『番』語者,十不過二三耳」(陳桂培 1872:306)。
相對於竹塹社共同組織的危殆,從守隘所吸取的寶貴經驗,卻使竹塹地區的平埔族人在乾隆末年之後,有能力積極參加保留區外的另一個地區,即隘墾區的開墾工作。例如霄裡社的蕭家之於明興庄,竹塹社衛家方於新興庄,以及竹塹社錢家之於金興庄等。最後並在這個地區開闢出一片雖不如土牛溝內外的土地那麼富庶,卻能充分證明自己的能力和存在,同時也是屬於自己的新天地(施添福 1990:87)。這意謂傳統的竹塹社的共同組織瓦解了,他們分散為各姓,融入地方村落,成為漢人社會之一員。
但是「竹塹社」仍然存在,只是改變了形式。這個形式來自客家,但是和屯田制度不可分割。西元1860年代(同治年間),竹塹社之共同祭祖已如客家常用之稱呼「烝嘗」,以每年的九十五份屯餉之部份租谷為春秋烝嘗祭祀之用。1878年建「采田宮」,亦稱新社公館,所謂采田,係因「番」從采田二字。1904年日人以補償公債的方式,廢番大租。竹塹社人變賣公債,再購水田壹處,作為祭祀公業(王世慶、李季樺 1995:134)。至此,竹塹社人以屯田組織及客家的祭祀公業方式,留住所謂竹塹社這個名字。直到1966年,竹塹社祭祀時仍用道卡斯語請祖先,只是這個竹塹社已非當年的竹塹社(王世慶、李季樺 1995:160)。而自此之後,道卡斯語也在人世間絕跡。所謂的竹塹社人,透過父系傳承,及采田宮的共同祭祀,以另外一種社會結構的形式生存下去。至於傳統的竹塹社文化,在現實社會中,已無從聞問了。
結論
竹塹地區的土地屬於竹塹社,因為這些草埔是他們狩獵梅花鹿的鹿場。但是作為可以成為水田的土地,竹塹社人對它的所有權,係來自於清政府對土地最高的支配權。然而,水田生產所需要的社會結構,不是道卡斯族固有的,於是只有求助於當地客家人;水田生產相對於遊耕的經濟利益,特別是隨之而來土地價值,這樣的商品經濟壓力也不是竹塹社原有社會結構所能承受的;商品經濟背後的文化背景,對竹塹社人而言,更是那麼陌生。在他們學會與漢人對抗之前,西元1733年,他們已經以區區
「給地、賜姓、與封官」對竹塹社人而言,無疑是一條「通往地獄的天堂之路」。它使竹塹社人無可奈何的附麗於執政者,但是卻無法成為統治階級,繼續在整個竹塹地區活動。就在這條路上,閩南及客家劫奪了道卡斯車上豐腴的土地財富。最後,甚至道卡斯人被迫離車而去,於是空盪盪的道卡斯車,默默的駛向歷史的彼端。
附語
關於平埔之研究中,以凱達格蘭、巴則海、西拉雅等較深入。然而道卡斯族的研究卻有一資料上的優勢:土地申告書,亟待發揮。雖然目前的研究已鉅細靡遺的將土地申告書中,所有關於竹塹社的文書資料蒐錄成冊,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卻忽略了可以從土地申告書所記錄的大租口糧名冊中,透過系譜關係的比對,復原竹塹社分界自耕時,各姓的分佈所在。這對竹塹社之社會結構變遷過程的重建,應有重要意義。[10]只有這樣透過進一步的研究,我們才能理解竹塹社文化,也才能進一步像思考西拉雅祀壺文化那樣,思考竹塹地區客家文化與道卡斯文化的合成現象。
參考書目
六十七居魯
1807
番社采風圖考。臺北:臺灣大通書局。
王世慶、李季樺
1995 竹塹社七姓公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見潘英海、詹素娟編:平埔 研究論文集,頁128-171。
李亦園
1982 臺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臺北:聯經。
李季樺
1989 清代「番兒至老而無妻」的原因初探──以竹塹社為例,臺灣史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
施添福
1990 清代臺灣「番黎不諳耕作」的緣由:以竹塹地區為例。民族所集 刊,69:67-89。
張炎憲、李季樺
1995 竹塹社勢力之衰退之探討,見潘英海、詹素娟編:平埔研究論文 集,頁173-217。
張炎憲、王世慶、李季樺(主編)
1993 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臺北:中研院臺史所。
張隆志
1990 族群關係與鄉村臺灣───一個清代臺灣平埔族群史的重建和理 解。臺北: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陳其南
1990 家族與社會。臺北:聯經。
陳培桂
1872 淡水廳志,臺灣:大通書局新刊。
黃叔璥
1724 臺灣使槎錄。臺北:臺灣大通書局。
黃富三
1981 清代臺灣之移民的耕地取得問題及其對土著的影響(上)、 (下),食貨月刊11(1):19-36;11(2):26-46。
黃應貴、葉春榮
1997 從周邊看漢人的社會與文化。臺北:中研究民族所。
黃應貴 編
1993 人觀、意義與社會。臺北:中研究民族所。
新竹文獻委員會
1954 新竹文獻會通訊,新竹:新竹文獻委員會。
潘英海
1994 文化合成與合成文化──頭社村太祖年度祭儀的文化意涵,刊於 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
戴炎輝
1979 清代台灣之鄉治。台北:聯經。
Lewis,
I.M.
1985(1976)社會人類學導論(Social Anthropology in
Perspective.)。黃宣 衛、劉容貴譯,臺北:五南出版公司。
Kottak,
Conrad Phillip
1997 Anthropology: the Exploration of Human
Diversity.
Shepherd,
John Robert
1993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Plattner,
Stuart
1989 Marxism, in Economic Anthropology, edited by
Plattner. Stanford Californi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 本文發表於「原住民與少數民族的社會文化論述:第二屆全國人類學相關領域研究生論文發表會」,台大人類學系主辦,台北:中央研究院,2001年6月2-3日。筆者時就讀於清華人類所博士班,本文充其量僅是篇讀書報告而已,後亦未再深入。辱承學術同好錯引,授課學生問及此文,爰張貼於個人部落格。
[2] 近來平埔正名運動方興未艾,長路漫漫,正待觀察。
[3]張隆志關於巴則海族群史的理解與詮釋提出五個課題與觀點:理番政策與基層社會及鄉治間的關聯影響、租佃契作制度與水稻生產技術在開發史上之經濟及社會意義、親屬及婚姻制度對於其在文化適應及變遷中的影響程、宗教信仰的選擇與其社會文化特質及歷史情境間的演變過程、族群關係及認同意識在不同時空及人文條件下的表現方式。
[4]日本學者這一分類與清代所謂「生番」「熟番」有直接關係,清代從漢文化立場出發,以「漢化」的深淺程度,作為分類的標準。日本學者則以居住地,作為南島語原住民之分類標準。這一平埔、高山的區分,一直沿用到今。然而這一區分也逐漸受到挑戰分,請參見「人類學在臺灣的發展,國際學術研會」之相關論文。
[5]關於平埔族的分類,首先由日據時期的日本學者伊能嘉矩與粟野傳之丞於西元1900年出版的「臺灣番人事情」,奠定初步的系統分類基礎。後起學者在這基礎上,多所修正,目前仍有許多不同的意見,未有定論。相關文獻請參考
[6]見於伊能嘉矩,臺灣蕃政志,1904:443-4。轉引自施添福 1990:80-1。
[7]此一形式的祖靈祭亦見於嘉義的和安雅族、埔里的貓霧揀族、臺中平原的巴則海族。李亦園將這四者合稱為「賽跑型」祖靈祭,見李亦園 1982:36-37。
[8]此一說法近乎權力上的傲慢偏執,但是卻又莫可奈何。就好像新大陸當然無勞哥倫布之渡海而後存在,但是純粹對西方人而言,新大陸確實是哥倫布所發現的。
[9] 筆者有位熟稔的友人,積極投入客家運動多年,也以客家為其自我認同。近年平埔意識的覺醒,頓時使他陷入認同危機。
[10]參見羅烈師 1997 清華碩士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