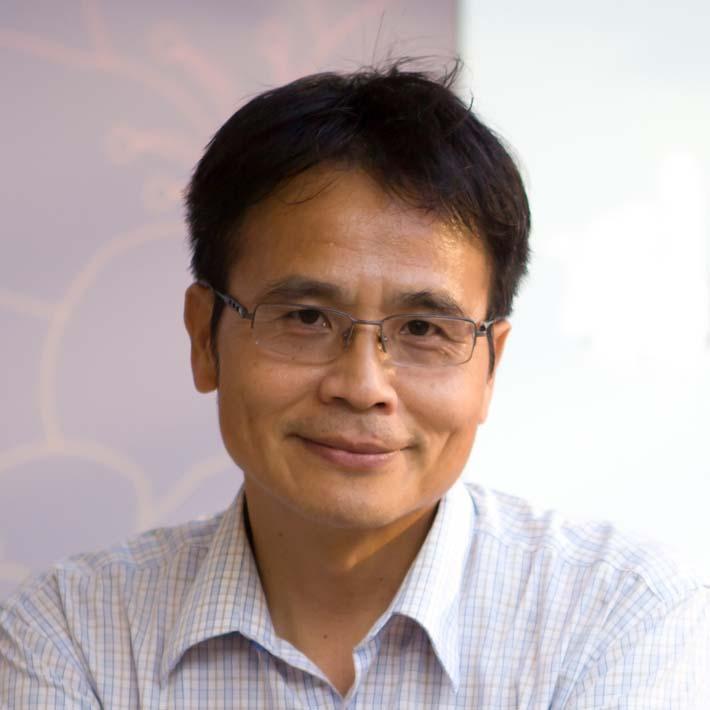•2014年4月22日 星期二,晚上10:23
鬧熱與族群:臺灣客家日與客家論述[1]
羅烈師
交大客院
一、前言:關女媧什麼事?
第一年全國客家日前夕,筆者致電某位客家長者,提及客家日活動相關事宜,長者先是語帶保留,繼而頗有微詞,最終火力四射,對全國客家日訂於天穿日頗不以為然地評道:「臺灣客家關女媧什麼事?」
反之,行政院客委會已配合民國一○○年農曆正月20日、國曆2月22日的全國客家日,透過大眾傳播媒體,以動畫形式向國民宣傳客家日的來源與意義,並且辦理各種慶祝活動,並邀請全國各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共襄盛舉。[2]
面對這判若霄壤的態度,本文企圖以當代臺灣客家族群論述的歷程,討論全國客家日之訂定所顯示的族群建構意義。筆者認為,政府為主導的全國客家日最終訂在天穿日,顯示當代臺灣客家族群的建構放棄了以抗爭為基調的社會運動象徵,而選擇了回歸傳統,同時也創造傳統的辦法。這一方面反映台灣客家欠缺一個共同又獨特的傳統節慶,一方面也顯示當代神聖性下降的特性,因此,重新建立一個共同的鬧熱,藉此凝聚客家族群意識。
下文首先簡述全國客家日之訂定與天穿日的源流;其次以當代臺灣客家族群建構的斷裂與延續兩種觀點,討論八項客家日候選名單;最後以抉擇於鬧熱或抗爭之間作結,說明當代臺灣客家族群建構的歷程是一個追求客家主體性的歷程,這一主體性在政治中得到實踐,卻也因此隱而不彰,天穿日之成為全國客家日,正好十分明確地投射出這一趨勢。
二、天穿日脫穎而出
立法院2010年1月5日三讀通過「客家基本法」,其中包含管碧玲等26人「明訂全國客家日」的提案修正,於是依法必須訂定全國客家日。[3]為此,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經過第一階段廣徵積極參與客家事務人士,以及第二階段全台客家鄉親意見調查後,於2010年9月10日宣布農曆正月二十日「天穿日」為全國客家日。
客委會基於三項理由,在兩階段調查後的候選清單中,最終選定了天穿日為全國客家日(行政院客委會2010)。這三個理由是天穿日具有客家文化獨特性,無族群排他性,又兼具國際視野。所謂獨特性係指天穿日是客家人獨有的特殊節慶,具深遠文化傳承意義;所謂排他性應指相對於其他候選名單,天穿日沒有對抗或排外的意涵;至於國際視野則是著眼天穿日不工作、休生養生息,古典女媧煉石補天的傳說,內含愛惜自然及環保等時代精神,是具有國際發展性的慶典節日。
三、天穿習俗其來有自
對筆者而言,天穿日不是陌生的名詞,但卻是個陌生的節慶。同時,陌生的不只是晚期戰後嬰兒潮的筆者自身,戰前出生的老人家也五十步百步之譜。
進一步追問,當天是否會舉行任何祭祀儀式呢?男人女人都沒有回應。經提示有沒有浮甜粄(po tian banˊ,炸年糕)拜天的儀式後,女人想了一會兒表示,從前好像聽老人家說過,但沒看過,自己也不曾拜過。
至於「為什麼天穿日不能工作,而且適合在井邊穿耳洞呢?」這一類打破沙鍋的問題,往往也很難得到答案。
追根究柢,其實天穿日源遠流長,是漢文化相當普遍,但卻未特別受重視的節慶。就時間而言,早在東晉(西元317-420)就有「補天穿」之類的風俗;就空間而言,從歷代地方志的記錄看來,無論華南、華中或華北都有類似的天穿、天川、田穿、天倉、添倉、填倉等習俗或傳說(常建華2006)。
前述為何天穿日「男人不工作,女人穿耳洞」的疑問,在廣大漢文化的地區傳統中也找得到類似的習俗。推究其緣由,應該是時值春雨,天穿地漏,此時工作不惟枉然,更屬不吉;至於穿耳洞於井邊亦然,既然天穿地漏,穿孔於薄薄的耳垂,自然簡單又安全。換言之,這種天穿習俗基本上是傳統數術的一環。
那麼為什麼漢文化普遍的天穿日習俗,會成為獨特的臺灣客家習俗,更進而而為全國客家日呢?這是單純的誤會嗎?筆者認為,無論實際的臺灣社會生活裡這是不是單純的誤會,對於觀察社會文化的研究者而言,如果僅以單純的誤會視之,必定簡化了問題。
四、堅持傳統的臺灣客家
促成臺灣客家認定天穿日為客家獨特習俗的原因之一是社會變遷速度的城鄉差距。
漢文化正月節慶的兩個主軸是春節與元宵,二者在漢文化民俗的普同重要性此處不贅述。值得再加強調的是元宵,也就是上元節,對於臺灣客庄,特別北臺客庄的重要性。
上元前後對於北部客庄而言有幾件重要神聖儀式,首先是許福儀式通常在上元辦理,搭配下元或年底的還福,成為客庄底層信仰基礎(羅烈師2008a)。這個儀式在不同客庄有著不同名稱,包含天神良福、天公福、及祈神等,但作為向天公(玉皇大帝與三官大帝)叩許酬還的意義則完全相同。
其次,北部客庄通常春節至中元之間南下北港朝天宮進香,北返之時,必定迎奉媽祖分身回庄,並於中元前後演戲慶祝,稱為媽祖戲(范明煥2005)。
簡言之,正當正月春節,尤其是中元花燈、天神良福及媽祖戲等,才大肆熱鬧過後,天穿日恐怕難以成為重大的節慶。
尚有進者,在當代臺灣普遍之商品化、工業化與都市化的緊湊又除魅(disenchanted)的生活氛圍下,天穿日習俗會被逐漸淡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只是對於特別堅持傳統的客家而言,天穿日這一傳統節慶,部份客庄長者倒是多留了一些記憶與儀俗,於是乃有天穿日是客家獨特節慶的感覺。簡言之,當大部份臺灣漢人都忘了天穿日之時,少部份沒有忘記天穿日的客庄及其長者,很可能就主張天穿日是客家獨特的節慶習俗。於是乎,當客家基本法明訂全國客家日後,天穿日因緣際會,列入了臺灣的客家日的候選名單。
五、亟須建立共同象徵的臺灣客家族群論述
如前所言,縱然天穿日被列入名單,為什麼最終會脫穎而出呢?這個問題所要的答案當然不在於追問行政院客委會關於全國客家日的決策過程,而是要從更深遠的臺灣客家族群論述的趨勢下,評述這一事件。
關於臺灣客家族群論述,學界所共識是建構論的立場。王甫昌(2003)認為族群不是一個具有一些共同的血緣或語言文化等本質性特質的團體,族群團體其實是被人們的族群想像所界定出來的。族群的特性包含:以「共同來源」區分我群與他群的一種群體認同;族群是相對性的群體認同;弱勢者認知與他群之間存在差異,而且感知我群受到不平等待遇,必須集體行動才能爭取我群權益;而族群的位階與規模介於國家(民族)與家族之間;族群是一種人群分類的想像,為的是與其他族群平等相處。這種族群認同是現代的產物,其具體族群分類類屬隨時間而有差異,其族群意識係社會運動所創造的,而且受到國家與公民概念所啟發,至於族群認同的功能則是提供了個人社會歸屬感以及對抗族群歧視的憑藉。臺灣客家作為一個族群,其論述即始於1980年代以降的本土社會運動。
相對於王甫昌對臺灣客家族群論述之社會運動面向的重視,羅烈師(2006a、2008b)則對族群建構之歷史基礎用力甚深。羅烈師認為,由於當代臺灣的客家現象勃興,而且政府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同時在學術方面,以民族主義為著眼的國族論述又持續醱酵,使得臺灣學界傾向於認定客家是當代臺灣特定政經環境的產物。然而當代臺灣客家現象係建立在傳統祖籍人群分類,尤其是成熟於十九世紀中期的粵人認同之基礎上。客家始於主客或土客之相對意義下的一般性分類,而且這個一般性概念遍及中國各地;至十九世紀時,兩廣完成了「客家論述」,臺灣則產生了「客人論述」;二十世紀中期以後,二者合流為客家論述;而全球性的客家論述便是這一合流在二十世紀最後三十年的傳播結果。
王甫昌的理論可以稱為「斷裂論」,羅烈師則是「延續論」,前者強調當代鉅變,後者則聚焦傳統。然而無論斷裂或延續,基本上皆屬建構論的視野,自然也會同意在族群建構過程中,必須動用共同的象徵,以畫分族外,進而凝聚族內。
用這兩種觀點,亦即當代與傳統,可以將行政院客委會之客家日前八名之候選名單,分類為二:
其一為當代客家運動時事紀念日,四者皆為國曆,包含:
客家基本法三讀通過日(國曆1月5日)
客委會成立日(國曆6月14日)
國父誕辰紀念日(國曆11月12日)
還我母語運動(國曆12月28日)
客家基本法三讀通過日(國曆1月5日)
客委會成立日(國曆6月14日)
國父誕辰紀念日(國曆11月12日)
還我母語運動(國曆12月28日)
這四項候選名單實際上以12月28日為核心,1988這一年12月28日的「還我母語」大遊行,揭開了當代臺灣客家運動的序幕,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其次,國曆11月12日的國父誕辰紀念日之所以列入名單,究其緣由因係還我母語大遊行的名譽總領隊正是國父孫中山先生,而且當日遊行隊伍中,刻意在國父遺相上戴上口罩,隱喻國父是客家人,國父的母語也被噤聲。至於6月14日客委會成立日以及1月5日客家基本法通過日,則可視為是客家運動的成果。簡言之,以上四者之入選皆與當代客家社會運動之因果密切相關。
其二為傳統習俗與節慶,四者皆為農曆,包含:
客家人掃墓祭祖日(農曆1月16日)
天穿日(農曆1月20日)
義民節(農曆7月20日)
還福收冬戲(農曆10月15日)
客家人掃墓祭祖日(農曆1月16日)
天穿日(農曆1月20日)
義民節(農曆7月20日)
還福收冬戲(農曆10月15日)
四項農曆候選日的共同特徵都是傳統儀式或節慶民俗,掃墓祭祖日係因相對於漢文化常見之清明掃墓,客家通常正月十六日至二月初間,即已掃墓;義民節則因義民信仰乃臺灣獨創的民間信仰,在北台客庄,特別是新竹與桃園有極高的重要性;還福收冬戲則因前述天神良福儀式在客庄普遍受到重視;至於天穿日前文已提及,不再贅述。
總之,八項候選名單隱然是國曆對農曆,當代對傳統,何者會被選為全國客家日呢?或者說,客家日的選定意謂著何種臺灣客家論述的趨勢呢?下文分別論述之。
六、運動與族群
以1988還我母語大遊行作為臺灣客家運動之序幕,2007年「臺灣客家研究學會」辦理客家運動20年學術研討會,會中發表的十六篇論文,後來亦由張維安、徐正光及羅烈師等擔任主編,集結成書,對客家運動之內涵、發展、影響及未來,大致勾勒出相當完整的圖像。
研究者依據史實,將運動分成不同階段,討論運動本身的轉變過程;客家運動之發展係始於族群政治,但其趨勢則為指向客家主體性之建立,而且這一主體性最能施力處為語言。這也就是「還我母語」大遊行之「我」與「母語」兩大訴求之最深刻的意涵(羅肇錦2008,邱榮舉與謝欣如2008,楊國鑫2008)。
也有學者聚焦於客家運動對於台灣之地方社會、信仰、認同與客家意象之影響,發現客家運動實踐的成果是促成中央政府調整其族群施政之體制,然而客家施政的影響在不同地區與不同事務間,歧異不小,而且對於客家在全台灣之相對弱勢局面之扭轉,尚待努力(蕭新煌與黃世明2008)。
至於親身參與運動的前輩則以第一手見聞忠實地記錄了二十年來,客家運動的艱難與折衝。這種艱難與折衝見表現為政治立場與認同的不穩定狀態,台灣客協與客家雜誌即是如此(張世賢2008,梁景峰2008,彭欽清2008)。客家運動的主旋律始終與政治之間千絲萬縷,無法分清,而客家運動參與者間的政治認同也總是存在歧見的(羅烈師2008c)。
12月28日與11月12日這兩個候選者以及1月5日與6月14日另兩個候選者,分別代表了客家運動的起點與終點,無論選擇了這四個候選名單的何者,其實都意謂選擇了社會運動作為建構客家族群的共同象徵。
然而,正如前述客家運動20年之研究者所呈現的結論,客家運動之發展係始於族群政治,但其趨勢則為指向客家主體性之建立。客家運動實踐的成果促成中央政府調整其族群施政之體制,但是對於客家在全台灣之相對弱勢局面之扭轉,亦尚待努力。而恐怕更重要的是,客家運動始終與政治之間相互糾葛,而客家運動參與者間的政治認同也總是存在歧見(林吉洋2008,羅烈師2008c)。
於是乎,這種歧見以及因為歧見以致無法彰顯客家主體性,使得臺灣客家難以選擇客家運動作為建構自身族群論述的共同象徵。實際事實的發展正符合這一趨勢,當代以國曆紀事的客家運動時事最終皆未能成為全國客家日,其實正意謂著臺灣客家族群的建構,已放棄了富涵社會運動氛圍的象徵。
七、鬧熱與族群
相對於國曆四項候選名單,農曆四項候選名單則明確地顯示了傳統面向。本來節慶係根植於文化傳統的,而且節慶通常有其神聖的氛圍,因此在節慶裡,眾人共同熱鬧地慶祝神聖的傳統,從而凝聚了集體意識。當代節慶的神聖性雖然降低了,但是鬧熱更甚,而且鬧熱往往成了神聖性的替代品,也相同地聚攏了原本陌生的人群。
四項農曆候選日中,義民節恐怕最受矚目,這一信仰乃臺灣獨創的民間信仰,在北台客庄,特別是新竹與桃園有極高的重要性,因此頗具代表性(莊英章1989、江金瑞1998、賴玉玲2005、林桂玲2005、羅烈師2006b、黃卓權2008);台北市客家各界與台北市府20年來亦隆重辦理義民祭典,甚至請來全臺義民爺共聚台北城,使義民爺儼然成為全臺客家神聖象徵(羅烈師2006c)。然而義民信仰雖被桃竹客庄以「褒忠」高舉,但是畢竟臺灣泉州人的「旌義」義民信仰與褒忠一樣源遠流長;苗栗與南臺客家對義民信仰其實關注不多;義民爺甚至還曾捲入「孤魂野鬼」與「義或不義」的爭執(楊鏡汀1998、林光華2001)。因此,作為族群信仰的義民節雖然呼聲頗高,但是仍存在著代表性、神格、政治正確等問題。
其次,掃墓祭祖日所顯現的對家族,特別是宗族的重視,也相當程度彰顯了臺灣客家族群相對於閩南族群的特質;同時,漢文化習俗通常於清明時節掃墓,臺灣客家則提前於正月十六日至二月初間,即已掃墓,亦有特殊性。可是由於掃墓之日客庄各個家族與宗族並不統一,難以指定其中一日為客家日。
至於還福收冬戲係客庄普遍受到重視的「許福還福」習俗,相對於年初的祈許,年底的賽還顯得更加隆重而熱鬧。近年行政院客委會配合鼓勵客家戲曲發展之政策,結合客庄與戲班,辦理收冬戲活動,也頗受矚目。然而許福還福儀式一來儘管普遍舉行於各地客庄,但是彼此之間並無聯合交流的現象,故不似義民節有龐大的人群凝聚現象;同時,各庄日期亦不一致,訂為十月十五日未必盡符各庄實情。
總之,傳統習俗確有凝聚客庄的功能,然而臺灣客庄傳統習俗之中,其實無法找到一個足以作為建構臺灣客家族群之共同象徵。
換句話說,尋找一個傳統節慶,作為建構臺灣客家族群存在著困難。只是吾人也不必誇大這種困難,其實傳統往往是被創造的(Hobsbawm 2002);這種因為欠缺傳統所以創造傳統的事例,在當代客家顯形的論述歷程中,其實也十分常見。例如擂茶成為客家標誌飲品,藍衫與紙傘成為客家用品,花布是客家布品等。尤其是行政院客委會所推動的桐花祭,於今十年有成,更已成為臺灣客家年度能見度最高的節慶。
客家日最終訂在天穿日,當然意謂當代臺灣客家族群的建構選擇了回歸傳統,同時也創造傳統的辦法。這一方面反映台灣客家欠缺一個共同又獨特的傳統節慶,一方面也顯示當代神聖性下降的特性,因此,重新建立一個共同的鬧熱,藉此凝聚客家族群意識。
八、結語:抉擇於鬧熱或抗爭之間
1988年底,臺灣客家運動發起,至2001年行政院客委會成立,這或許算是客家運動的成功吧!然而,弔詭的是,政府至此掌握了客家的發言權;或者反過來說,似乎所有客家事務都被認定是政府的事,而且是各級客委會或客家事務單位的事。結果客家運動當年想要喚起的客家主體性(張維安、徐正光與羅烈師 2008),有點詭異地化身入政府,至此若隱若現,欲走還留。
筆者以為,全國客家日的訂定,基本上就是依循著這樣的軌跡。以社會運動為起點,卻走入政治終點的客家主體性,在抉擇其自我建構的集體象徵時,捨抗爭而取鬧熱,幾乎可以視為是必然的結果。又由於欠缺全體臺灣客家節慶的共同象徵,候選節慶各有優劣限制,結果名單中與實際習俗淵源最淺,當然包袱也最輕的天穿日,在無族群排他性,又兼具國際視野的說法下,脫穎而出。
既已抉擇了節慶,而且又必然籠罩在施政成果、文化產業及觀光行銷等考量下,客家事務恐怕難免就有了幾分等待非客家之他者前來觀看的味道。然而,這種以觀光手段推展族群文化的策略,其實是兩面刃,不得不慎。
對於彼此平等的觀光客與觀光主(參觀者與被參觀者)而言,透過觀光將會有主客之間的結盟關係,而且觀光主自身對觀光事業便有比較強大的主導力量。例如觀光就被視為是歐洲國家「歐化」(Europeanization)願景的五個力量之一(Borneman and Fowler 1997);德國的羅騰堡(Rothenburg ob der Tauber)在納粹執政期間,是納粹信仰的表徵,當地居民及城鎮就藉由這象徵,使之可見、可感、可消費(Hagen and Joshua 2004)。
反之,當觀光主客之間的權力關係極端不平等,幾乎就是一種文化的帝國主義(Nash 1989);東非洲的研究者透過檢證觀光、權力與認同三者交互關聯的過程,發現Tanzania的Zanzibar地方觀光事業的特質,實際上是被新殖民主義與文化帝國主義所決定的(Borneman and Fowler 1997);而在中美洲宏都拉斯Garifuna村落的地方觀光經濟持續增溫的過程中,當地居民直言正苦於文化消逝(culture loss),因為他們根本無法透過觀光而控制文化的商品化(Kirtsoglou and Theodossopoulos 2004)。這無疑宣告了,對弱勢地區而言,觀光等同是來自於強勢地區一種政治統治或商業宰制的文化手段。
總之,當代臺灣客家族群建構的歷程是一個追求客家主體性的歷程,這一主體性在政治中得到實踐,卻也因此隱而不彰,天穿日之成為全國客家日,正好十分明確地投射出這趨勢。
對於這一趨勢,吾人一則以喜,一則以憂。至於會不會有一天質疑女媧的長者能從中見喜,而廟堂諸君則審知長者之憂,則盡付光陰吧!
參考書目
Borneman, John
and Nick Fowler
1997 Europeanizatio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6 (1):487-514.
1997 Europeanizatio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6 (1):487-514.
Hagen, Joshua
2004 The Most German of Towns: Creating an Ideal Nazi Community in Rothenburg ob der Tauber.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94(1): 207-227。
2004 The Most German of Towns: Creating an Ideal Nazi Community in Rothenburg ob der Tauber.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94(1): 207-227。
Kirtsoglou,
Elisabeth and Theodossopoulos, Dimitrios
2004 They are Taking our Culture Away.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24(2):135-157.
2004 They are Taking our Culture Away.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24(2):135-157.
Nash, Dennison
1989[1977] Tourism as a Form of Imperialism. In Hosts and Guests: 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Valene L. Smith ed. 37-52.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9[1977] Tourism as a Form of Imperialism. In Hosts and Guests: 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Valene L. Smith ed. 37-52.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王甫昌,2003,《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
江金瑞,1998,〈清代臺灣義民爺信仰與下淡水六堆移墾活動〉。臺中:中興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0,〈全國客家日公布 「天穿日」脫穎而出〉,張貼於行政院客委會官方網站2010/9/10之最新消息,網址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94091&ctNode=2159&mp=2013,2011/2/7登入。
林光華,2001,〈他們有主!〉,刊於鍾仁嫻編《義民心鄉土情》,頁2-4。新竹:新竹縣文化局。
林吉洋,2008,〈臺灣客家認同與其承擔團體: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1990-1995)的發展與政治參與〉,刊於張維安等編《多元族群與客家:臺灣客家運動20年》,頁370-400。新竹:台灣客家研究學會。
林桂玲,2005,《家族與寺廟: 以竹北林家與枋寮義民廟為例(1749-1895)》。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縣文化局。
邱榮舉與謝欣如,2008,〈臺灣客家運動與客家發展〉,刊於張維安等編《多元族群與客家:臺灣客家運動20年》,頁95-132。新竹:台灣客家研究學會。
范明煥,2005,《新竹地區客家人媽祖信仰之研究》。新竹:新竹縣文化局。
張世賢,2008,〈臺灣客家運動的起伏與隱憂〉,刊於張維安等編《多元族群與客家:臺灣客家運動20年》,頁299-334。新竹:台灣客家研究學會。
張維安、徐正光與羅烈師編,2008,《多元族群與客家:臺灣客家運動20年》。新竹:台灣客家研究學會。
梁景峰,2008,〈風雲1987一客家風雲雜誌創刊的時代背景和藍圖〉,刊於張維安等編《多元族群與客家:臺灣客家運動20年》,頁335-345。新竹:台灣客家研究學會。
莊英章,1989,〈新竹枋寮義民的建立及其社會社會文化意義〉,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民俗與文化組。南港:中研院民族所。
彭欽清,2008,〈從“解嚴”的《客家風雲》到“戒嚴”的《客家雜誌》〉,刊於張維安等編《多元族群與客家:臺灣客家運動20年》,頁346-369。新竹:台灣客家研究學會。
黃卓權,2008,〈義民廟早期歷史的原貌、傳說與記載--歷史文本與敘事的探討〉,刊於《臺灣文獻》,第59卷3期,頁89-127。
楊國鑫,2008,〈臺灣的客家問題、客家運動與客家學〉,刊於張維安等編《多元族群與客家:臺灣客家運動20年》,頁133-153。新竹:台灣客家研究學會。
楊鏡汀,1998,〈義民爺為何變成孤魂野鬼?--從歷代志書探討義民神格被貶的經過〉,刊於《客家雜誌》,第95期,頁43-46。
蕭新煌與黃世明,2008,〈臺灣政治轉型下的客家運動及其對地方社會的影響〉,刊於張維安等編《多元族群與客家:臺灣客家運動20年》,頁157-182。新竹:台灣客家研究學會。
賴玉玲,2005,《褒忠亭義民爺信仰與地方社會發展:
以楊梅聯庄為例》。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縣文化局。
霍布斯邦(Hobsbawm,
E. J)等,2002,《被發明的傳統》(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臺北:貓頭鷹。
羅烈師,2006a,〈臺灣客家之形成:以竹塹地區為核心的觀察〉。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2006b,〈臺灣枋寮義民廟階序體系之形成〉,刊於《客家研究》,第1期,頁97-145。
----------,2006c,〈揮汗挑擔,再祭義民--從傳統鄉村走到現代都會的義民信仰〉,刊於《新活水》第8卷,頁98-103。
--------,2008a 階序下的交陪:一個北台灣客家村落的媽祖信仰。發表於「第二屆台灣客家研究國際研討會:客家的形成變遷」,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舉辦,12/20-21,台灣新竹市。
----------,2008b,客家概念的起源、形成與傳播大綱。發表於「2008台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年會」,台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舉辦,10/4-5,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08c,〈導論:多元族群與客家〉,刊於張維安等編《多元族群與客家:臺灣客家運動20年》,頁1-7。新竹:台灣客家研究學會。
羅肇錦,2008,〈以「祭國父文」反襯中山先生與客家運動的破與立〉,刊於張維安等編《多元族群與客家:臺灣客家運動20年》,頁11-34。新竹:台灣客家研究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