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25日 星期二,晚上9:38
楔子
1983年童養媳阿蘭(1937-)跟丈夫阿牯(1935-)買下了同在老街的舊房子,這是她個人生命的高峰,同時,一個大家庭至此分支為二。
阿蘭
阿卡桑[1]與阿婆[2]
昭和十二年(1937)阿卡桑(1912-1997)生下第三胎,這個男孩出生後不久,便不幸夭折,家庭籠罩著不安。其實後來我們知道,阿卡桑是多產的女子,終其一生生了十一個小孩。多產意謂著多奶,新生兒夭折,便萌生應該再抱一個小孩來吃奶的念頭。「阿滿仔,厓買一个媳舅仔分汝,好麼?」[3]她的家娘問她,但阿滿仔答應與否並不重要。原來,十年前家娘與家官買下兩間店面建築,一家人從山裡遷來街上,開店為生。但家官早逝,家裡的事情都由家娘決定;更何況這家娘的脾氣是遠近皆知的。
家娘的同姓宗族在老街附近的南勢是個大姓人家,便透過這樣的同宗關係,一位伯姆作媒,找到了同宗族一位嫁到楊梅的女兒。她才剛生下了第一胎三個多月,身體欠安,她的生母就勸她,把這長女賣到老家。
於是就在吉利、奶水與幫手等多重考慮下,老街這家的女主人透過自已出生家庭的人際網絡,為自己的媳婦抱回來一個襁褓中的童養媳。這小嬰兒名叫梅蘭,她一輩子都被喚為阿蘭。
田寮
阿蘭的養家有地方知識份子的傳統,從來臺祖以來五代,一直是地方禮儀、契字文書乃至仲介折衝的角色。阿蘭的阿叔[4](1904-1991)兄弟倆是第五代子孫,也都保持了這一知識傳統。哥哥寫得一手好字,常替鄉人撰寫春聯、神龕、契字等;還參加詩社,吟詩作對,頗有傳統地方知識份子的身影。弟弟,也就是阿蘭的阿叔,雖然不若哥哥才情,但傳承了地理、擇日、排八字等傳統知識,被鄉里尊稱先生,紅包所得總是超過哥哥筆潤。不過,令人略有意外,這一紳士的身份並未使蘭家買得半畝田園。
昭和二年(1927)阿叔與兄長隨父母遷居老街時,尚未有子女;至光復初期,兩兄弟各育有四男及五男三女。起初這家庭經營米店,也仲介土地房屋買賣,略有餘貲,則放貸收息,在老街算是中上之家。不僅養得起一大家子,還擁有老街四間店面。
進入戰時體制後,實施米穀配給制度,米店經營不佳,甚至賠掉大筆積蓄。戰後,阿叔兩兄弟佃耕了一塊兩甲左右的水田。民國三十七年(1948)阿叔的兄長留下老街一間店面給阿叔,賣掉其餘。自己帶著妻小,遷居到在佃耕田園處起造的家屋。由於房子簡陋,就稱為「田寮」。而兩個分戶的家庭賴以為生者,就是這兩甲田園。
此後,臺灣逐漸進入「進口替代」與「加工出口」的輕工業化時代。兩個家戶逐漸成長的子女一個個離開家戶,出外工作;但各留下一個兒子為主要的水田耕種者。至農忙時節,兄弟姊妹才返家協助插秧或收割工作。
衣、水、柴
阿蘭被抱養之後十八年間,阿卡桑又先後生了四子四女。阿卡桑手巧,有不錯的女紅技藝,打出來的盤釦,總能得到鄰人的讚賞;生養孩子多了,又是先生娘,正是所謂好命婆,挽面行嫁,難不倒她。
但一家生計並不容易維持,阿卡桑在老街廟後租了約半分菜園,挑著木桶長杓淋菜,是每天必見的形象。同時,洗滌自家衣服外,爾偶還承攬鄰里臨時洗衣工作。自來水接通前,遇著旱季,家戶井水不夠深,打不到水時,還要前往街頭公眾大井挑水;當然也爾偶為無力挑水的鄰里挑水,賺取微薄收入。
隨著阿蘭長大,洗衣挑水等事情,就逐漸由阿蘭接手了。洗衣是每天例行的事,通常一大家子,包含阿婆、阿叔、阿卡桑、八個兄弟姊妹等人全部的衣服,全都是阿蘭的事。這些衣服悉數塞進兩個錫製水桶中,挑到溪邊水堀中洗滌。
很多時候,阿蘭除了洗這一大家子的衣服外,往往也還會承攬洗濯別人家的衣服。最常見的是街上懷孕後期與坐月子的婦女,無法洗衣時,就會付工資請阿蘭洗衣。這種情況又因老街近裝甲營區,外省人口不少,這些移民家戶人口不多,欠缺人手幫忙,增加阿蘭賺取工資的機會。
相同的是挑水這件事,阿蘭固定為街上一家飲食店每天挑滿水,按月給付工資。阿蘭初次領得工錢後,拿給阿叔,阿叔表示這是阿蘭的辛苦錢,就留著自己用,並未拿阿蘭的錢。於是對於這些賺取額外工資的機會,阿蘭十分賣力,所賺得的工錢就存入自己郵局的戶頭。
除了照顧年幼弟妹外,體力勞動是阿蘭最鮮活的形象。老街近山,日本統治期間鼓勵在低海拔山丘種植相思木,用以燒製木炭,因此整座後山都是相思木。由於燒炭所用木材部位為樹幹,樹枝則可直接用作家庭燃料。為了節約家庭購買煤炭或木炭的開支,阿叔常常要阿蘭到後山撿拾枯枝,整擔挑回家中後,再分剁綑成細束燃料。
阿牯
阿蘭十九歲那年(1955),四十四歲的阿卡桑生了個女兒,也是她最後一個小孩,而阿蘭也已到婚配的年紀。說來令人心酸,其實童養媳入戶當年,兩家已言定,阿蘭成年後,將許配給阿叔的長子(1933-)為妻。然而,當圓房的日子越來越近時,長子明白表示拒絕這一婚姻。長子相當程度傳承了家中作為地方知識份子的特質,一方面完成了中學教育,也一方面也正學習阿叔的擇日與文書專長。而且長子已有中意的女子,甚至最後不惜離家出走,就是不肯與阿蘭,這位他從小一起長大,但專做粗重工作的文盲妹妹結婚。
阿牯此時已是家中的勞動力支柱,佃耕的兩甲田地主要就是由他與堂兄兩人負責。
長子先是服役,繼而又離家到桃園工廠上班,幼弟皆未成年,個性老實的他,答應了阿婆的要求。就這樣,19歲的阿蘭嫁給的她的二哥,在那年的年三十(農曆年除夕)圓房。
結婚前後幾年間,年輕的阿牯除了自家田園外,四處打工,舉凡山裡抽竹劈林、插秧收割、製茶採柑等,只要有人徵工,便賣力前往。幼弟則嘗試不同行業學徒,三弟曾在老街外的新商業區租屋經營洗衣店,生意不佳後,離家北上進入工廠上班。五弟亦略同三弟,也赴臺北工作。倒是四弟先是學習摩托車維修,服役又在機場工作,學得不錯的機械知識與技能,於是在老街外的縱貫路上,租屋經營機車自行車修理店;而阿牯也一同經營。
買
此後十年間,阿蘭生養了兩男兩女。阿蘭的長子誕生那年(1960),阿婆過世,大家庭的經濟由阿叔打理。
阿蘭兄弟姊妹成年後,外出工作、結婚或出嫁,大家庭並未真的分家,但是已婚兄弟姊妹則陸續分戶而出,而留在大家庭的則為阿牯與四弟兩個核心家庭。大家庭的開支由佃耕的田園、阿叔自己擇日的紅包收入、外出工作的阿蘭兄弟姊妹每月固定繳回的部份薪水等支付。
除了主要耕種工作外,阿牯與四弟共同經營一家摩托車與腳踏車修理店,收入亦繳回阿叔。簡言之,這是個共財共居共生計的大家庭。而對於阿蘭的核心家庭而言,除了她微薄的洗衣挑水收入外,沒有任何積蓄。
拼紙炮仔
1968年阿蘭大女兒(1957-)小學五年級的暑假,是個改變的開始。
村內一位週日兼差到老街賣菜的爆竹工廠女工,在阿蘭家門前擺了菜攤。阿蘭詢問能否介紹自己的大女兒去工廠打工;次日,女兒就去上班了。之後女兒每到寒暑假,便到這工廠打工,賺取了自己直到高中所有的學費。隔年(1969),三十三歲育有兩男兩女的童養媳阿蘭,也進入這爆竹工廠,正式成為有固定薪水的職業婦女;而這「拼紙炮仔」(pin zhi pau u)的工作,她做了十八年(1969-1987)。
紙炮仔是爆竹的客語,拼是交纏拼合的意思,例如馬尾式的頭髮即稱為毛拼,這是當地鞭炮工藝的最後一道流程。1960年代起,幾乎有三十年的時間,老街所在鄉鎮是臺灣重要的地下爆竹工廠所在地。這工作有相當程度的危險性,但也養活了不少老街人。
傳統的鞭炮製作過程分為「炮身製作,火藥製作和引線製作」等三部分,其中火藥與引線都向批發商購買,工廠真正的工作是炮身的製作。
工廠裁紙之後,將捲製炮身的工作外包到家戶,這是那個年代老街男童最常見的家庭代工。工廠自家戶收回炮身空筒後,束成圓餅狀,對切之後,填入火藥,再以黃土封底,並釘入引線,便大致完成了餅狀而兩兩成對的爆竹。
所謂拼紙炮,通常亦稱作結鞭,亦即用引線將爆竹結成一掛。因為形狀像鞭,所以會有鞭炮之稱。阿蘭與四五位同事們便在這三五坪大小的房間裡,將一對對爆竹拼成鞭炮。這樣的工作清一色由女人擔任,且係論件計酬,工作期間只見工人熟練地重覆單調的動作。正因為熟練,她們的身體充滿律動,也還可以不時聊天,排解工作的枯躁。
這一拼紙炮的工作成為阿蘭的職業,也幾乎是她與阿牯組成之核心家庭唯一可支配的收入。
間房
阿蘭結束無薪的家務操持,成為有固定月薪的工人的前後幾年間,養家的弟妹們陸續結婚了。對於家屋而言,每一樁婚姻都意謂著一張張獨立的八掛床,甚或一間間獨立的房間。
老街是兩層樓狹長形店面式建築,佔地約四十坪。樓下前半是店面,後半及樓上則須滿足起居餐飲臥寢等需求。屋後有空地,類似合院式建築的天井,兼具通風採光休憩等機能;最後端則往往搭建矮寮,作為浴廁雞棲豬欄等。
在這樣的店屋中,夫婦會有自己的八掛床;而未婚子女則可能睡在一個大眠床,或男女分睡通舖。阿蘭結婚時,在二樓擁有了自己的八掛床;其他未婚弟妹則分別睡於同在二樓的兩張大眠床上;另外,二樓的最前端則有奉祀祖先的神明間;至於阿婆、阿卡桑與阿叔的兩張床舖則在一樓。
三弟結婚時,勉強將二樓後端的通舖,改成一間新房,並在二樓中段多隔了個閣樓,增加通舖,作為未婚弟妹及阿蘭先後出生的四個孩子的眠床。待四弟要結婚時,老街這店屋已確定無法容納新婚夫婦,於是便將天井及浴廁豬圈等,改建為一層平房,內有兩個房間,做為四弟新房,並預留五弟新房。
但三弟與五弟婚後皆離家工作,最終分戶而出;而姊妹們也都出嫁了。於是這房屋的空間使用情形成為阿卡桑阿叔老主人夫婦在一樓;阿蘭阿牯核心家庭在二樓;四弟核心家庭在天井增建之一樓。
1982年,阿蘭的長女出嫁,而長子與次子亦已成年。二樓這空間顯然不可能再容納兩個核心家庭,更甭提四弟也先後生了三子一女。
這個由阿叔掌握經濟的擴大主幹家庭,已經面臨居住空間不足,必須分戶的局面。毫無疑問,一些生計與家務分攤等大大小小瑣瑣碎碎,必然會加重這樣的壓力。
在阿蘭的記憶中,她那幾個禮拜裡,前前後後問了五次,阿叔先是沉默不語,繼而吞吞吐吐,就是不置可否。阿叔的心情為何,已無從得知,但阿蘭認為阿叔是「驚出錢」,因此不願答應,以免要共同負擔購屋款項。最後,阿叔只反問阿蘭哪來的錢買屋,但實際上並未不反對阿蘭的決定。
做會頭好贏[10]
於是阿蘭鐵了心要買下這房子,建立一個新的家庭。工作了十三年後,阿蘭其實有一筆存款。
一如眾多臺灣鄉村或人際互動較密切的都市社區或職場,標會是十分常見的理財方式。雖然終其一生阿蘭至少被倒會兩次,僅拿回部份會款,但標會仍然幾乎是她唯一的理財方式。
對於薪水不高的她,每個月只能跟一個會。決定要買屋的前一年,阿蘭得到十萬元會款。這個會的成員都是阿蘭熟悉的人,包含工廠的同事、兄弟姊妹、親戚及鄰居等。阿蘭得到這會款後,工廠一位處理火藥的男同事表示能否將這款項借給他,他會付利息。
其實這種借錢的事,阿蘭有過悲慘的經驗。青少年起阿蘭挑水賺得的工錢都存在郵局,一位親戚借去,甚至未付利息,最後竟然無消無息,阿蘭好幾年的血汗錢就這麼化為烏有。也不知為什麼,阿蘭還是把錢借給了同事。
幸好決定買屋之時,阿蘭順利地拿回這十萬元,籌到差不多一半的房款。另外一半,阿蘭想到的第一個辦法是工廠的老闆娘。老闆娘並未答應借錢給阿蘭,但是表示願意協助阿蘭招一個會,並讓阿蘭當會首,這樣就能籌到10萬元了。
對於一個文盲的童養媳而言,這是難以想像的事。擔任會首要先湊足會腳,這似乎不見得太難,但是要成為一群會腳的負責人,則令她膽怯。其次就要出具會單,要列出會友名字,還要熟詣標會規則,並形諸文字,這對文盲的她,根本是天方夜譚。至於每月主持標會,收繳會款,除了實質的執行能力外,當然也需要書寫與計算的能力。
這一切本來是超過阿蘭能力的,但阿蘭說,為了籌錢,她的膽子很大,接受了工廠老闆娘的建議,當起了會頭。會腳包含工廠同事、兄弟姊妹、親戚與鄰居等,很快就招滿了。此時已經退伍的長子幫忙處理文書工作,製表、謄錄、再拿到街上影印,完成了標單。分送名單,同時收滿會員的第一次會款後,阿蘭就籌齊了另一半屋款。
20萬之外,尚不足4萬元,阿蘭分別向阿卡桑及阿叔各借得兩萬元。就這樣阿蘭與阿牯騎著一臺摩托車,到街上的代書事務所,與屋主簽訂了買賣契約,正式買下了自己的房子。
屋
然而,阿蘭所買下的,僅是一間破舊的房子。
一如阿叔的老家,它的前半是兩層樓建築,只要修葺屋瓦、裝潢隔間、添購傢俱,即可居住;但是天井以後的加建部份,閒置太久,廚房浴廁飯廳等,皆無法使用。也就是說,阿蘭一家想要住進這新居所,恐怕還要再花一大筆錢。
就這樣,買屋的阿蘭變成了起屋的阿蘭;而關於起屋這件事,阿牯則幫了大忙。
對於阿牯與阿蘭而言,起屋不是件陌生的事情。從年輕就做雜工的阿牯,練就一身本領,加上農夫的強健體魄,成了很優秀的建築小工。當年在老家,四弟結婚而需加蓋房屋時,兄弟即以僱工購料的方式,建好了老家天井的房子。
老街街頭有個泥水師父叫阿田師,阿牯以日薪500元請阿田師為起屋的大工,並帶200元小工一人,同時自己也當小工,展開了起屋之事。阿田師看了屋況後,建議先完成天井加建部份的拆除工作,並且打掉原初天井與家屋交界的後牆;完成之後,再通知他,起屋之事才正式展開,也才需要付他工錢。
阿牯一人扛起了這件事!對於身兼農人與工匠的他,家中本來就不乏各式基本工具,他爬上屋頂,掀掉屋瓦,拆去桁架,最後卸下屋樑,頓時天井重見天日。圍觀也幫點小忙的鄰居,半要半搶又帶戲謔地拿走了桁樑,準備搭建自家的瓜棚;遍地殘瓦則將用以填高地基,不必清運;最後敲下的泥磚則用獨輪車,運到屋後打碎轉做菜園土。
阿田師開工之後,首先完成經始,畫定了地基與樑柱的位置;又估算了水泥、砂石及磚塊的數量,由阿牯自行訂購。挖地基及預伴水泥砂漿等事,阿牯天未亮便開始工作,待阿田師及他的助手到來時,很快便完成了地基工程。
接下來的釘板模與綁鋼筋工作,以4000元一坪,外包給另外一位老街附近的建築工頭。其次是灌漿工程,相較於前次建屋經驗,這一工作已由高壓灌漿車取代人工預拌。
當水泥乾硬,拆除板模後,房屋已具芻形。阿牯訂好紅磚,也陸續挑進屋內,還跟著阿田師及幾個小工,砌上外牆及隔間牆。而這同時,對水電也頗有概念的四弟也來協助埋設水電工程的管線。有一天,一樣住在老街的親家母,也就是大哥的岳母來到這整建中的房子,用責怪但眷顧的語氣問阿蘭:「仰會毋起二棧喏?」[11]阿蘭立刻回說連一樓的錢都快籌不到了,哪來的錢蓋二樓?親家母隨即建議,其實蓋二樓不用多少錢:「摎若大哥借!」[12]
此時,大哥在桃園的鐵工廠工作多年,已是廠長,家中經濟環境不錯。阿蘭的會他也參加了,便答應就將阿蘭會款標下,無息借給阿蘭;還表示錢不夠再找他。
最後的裝潢工程,阿牯在四弟的協助下,隔間、天花板及舖設部份地板都是自己動手,只有大型隔間與儲物兩用櫃是向街上的老木匠訂製的。
在1983年初,全新的兩層樓家屋完工。趕在農曆年前夕,阿蘭一家人依吉時轉開大灶瓦斯爐,象徵性地加熱了鍋中湯圓後,全家共食,正式搬進新家,也至此從她的童養媳養家,分戶而出。
跋
1999秋天,九二一地震撼動整個島嶼,老街也略微受傷,原本裂開的磚拱,更形嚴重;而阿蘭老家二樓的神明廳也因此令人擔心。
神明廳供奉觀音、關爺與祖先牌位,其中祖先牌位包含來臺祖以下六房中的四大房祖先們。雖說是四大房,其實有三房人丁不旺,由丁口最盛的第三房過火兼祧,等於就是第三房的神先牌位。[14]阿蘭的養家正是第三房,當年阿婆阿公帶全家遷居老街時,祖先牌位便隨著供奉於阿蘭的養家中。
一年七次的共同祭祀時,共有三十餘付牲儀擺在供桌前,與祭的宗族成員也有三四十人。老街樓層板是木造的,牆是泥磚所砌,而磚拱則有裂縫,族人難免擔心神明間樓地板承重的問題。
退休的阿蘭有一筆勞保退休金七十萬元,便悉數拿來修建二三樓;隔年,阿公婆牌便遷來阿蘭家的三樓頂。
從這個童養媳買屋的故事裡,我們看到臺灣1930-1980年代大家庭維持生計及分戶的過程。故事顯示男人的勞動力及所得由大家庭掌握;女人在臺灣輕工業化過程中,所賺取的薪資,反而成為分戶的動力。
最耐人尋味處在於,由於年長童養媳對養家幼弟妹的長期照顧,創造了以童養媳為分戶後各家庭凝聚宗族關係的核心。甚至分戶之後17年,宗族牌位最終安奉在童養媳的家戶。
簡言之,阿蘭買屋這故事,提供我們檢視傳統宗族的婦女視角。
[4]爺、爸、或爹等父親的稱呼在二十世紀前半的老街並不常用,反而以旁系尊親的「阿叔」稱呼父親;相同地也以「阿嬸」稱呼母親。與阿叔並用的稱謂是おとうさん,但通常省稱為とうさん,目前台灣現行通俗漢字寫成多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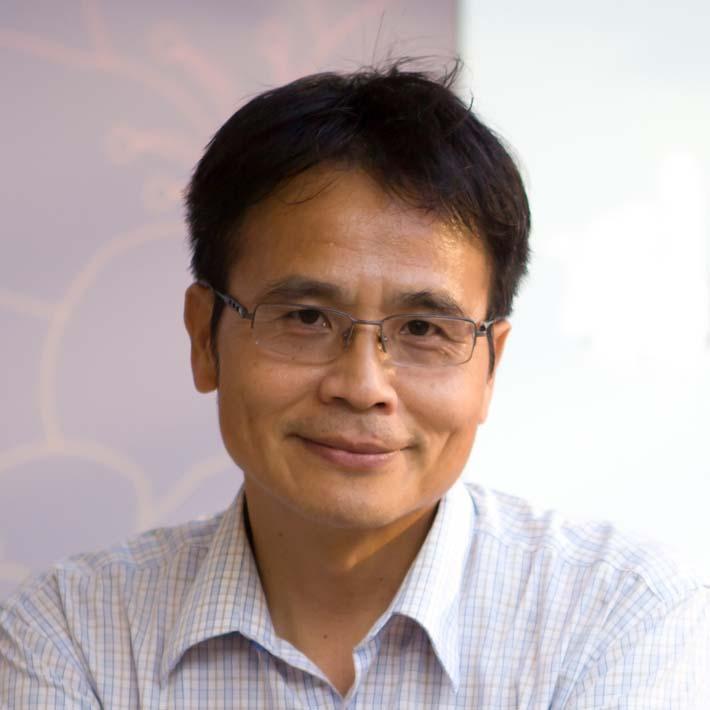

0 留言: